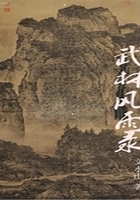
第11章 旧仇宿怨
淳于和见自己拿出令牌,淳于家众人连同淳于中都跪倒在地,更为得意,看着俯首跪在地上的淳于中道:“我尊你,便叫你一声二叔,不尊你,只当你是淳于家一般家仆一般,今日大敌当前,你打我那一下,我且不跟你计较,我现在命你带领淳于家人众,即刻将这些害我吃了许多苦头的仇人拿下,那思玉姑娘却不能伤了分毫!”
淳于中跪在地上,听淳于和发令,一脸痛苦无奈道:“淳于中尊令”,说罢站起身来,看着身后犹豫不定的淳于家众人道:“你等先护住家主,待我上前先跟这位广平兄弟做个了断,若我有甚么闪失,你们护着家主先退”,那淳于家众人此时也不知如何是好,都是一脸怒气的看着淳于和,淳于和却不耐烦道:“护甚么,我们这么些人,还斗不过他们区区十多人么,都给我上罢”
“淳于和!”刚刚站起身来的淳于中一声怒喝,淳于和惊的头一缩,将那铜牌高高举起神色惊慌道:“你想做甚么?难道要违抗家主之令么?”淳于中看着那铜牌,叹了一口气,语气却十分坚定道:“当家,我们身在江湖,自然要讲江湖规矩,你父亲死在这人手上,就算要今日要拼个你死我活,也须得跟他有个了断才是”淳于和见淳于中如此说,看了那第三家家仆一眼道:“也罢,你先料理了他,不过你若输了的话么……”说着从一个门人手中抢过一把单刀来,扔在地上道:“不用我多说甚么罢”
淳于中听了侄儿这句话,垂头丧气摇了摇头,走到那家仆身前道:“当家的有命,在下不敢不尊,还请足下不要见怪,当日我大哥死在你拳下,我今日也来领教领教”那叫做广平的家仆却看也不看淳于中一眼,冷冷道:“拿来”,淳于中一愣,当即明白是那一纸生死状,双手递上前去,那家仆一把拿过来,三两下扯成碎片,傲然说道:“就当我不曾立过此状,老爷子请动手罢,无论生死绝不皱眉”,他这一下举动,淳于家百余人顿时羞愧无地,心知此事传扬出去,淳于家在江湖上再无颜面见人,人人都敢怒不敢言看着那趾高气扬的淳于和,淳于和到似乎浑然不觉,见那家仆将生死状撕的粉碎,当时大笑道:“哈哈,既无证人,又无状书,这可不是我们不顾江湖道义,淳于中,你还愣在那里做甚么?”
淳于中回头看了一眼大呼小叫的淳于和,转回头来站了片刻,说了一声得罪,忽的双手一分,十指如钩,中宫直进,径取那家仆胸腹要害,那家仆也不怠慢,身形一退,腰腿微曲,吐气开声,呼的一拳,竟是要以拳对爪,淳于中不等招式用老,立刻收招转身,脚步一动,双爪连连挥出,始终不与那家仆双拳相对,只是前后左右不住的围着那家仆游走。
两人斗了近百合,那淳于和在一旁看的喜上眉梢,淳于中身形越来越快,犹如一头猛鹫搏食一般,双爪只是不离对手上三路要害之处,那家仆却步法凝滞,只是遮拦招架,如同被大鹰扑袭的野兽一样,只是护住要害,半天才攻出一拳。
余辽在一旁看了半晌,见那淳于中爪力到处,那家仆身上衣衫都被划成一道一道,满天的布屑乱飞,心想再这般斗下去,看来这家仆必然要伤在这淳于中手下,扭头看看师父,就见癞和尚也看着他笑道:“这般高明功夫,我不大看的出来,那边自有高手,你不妨请教请教”说着向那麹管家一努嘴。不想麹管家却笑道:“大和尚惫懒的可以,连指点徒弟都要别人代劳”说着走过来,看着余辽,一指那家仆道:“辽哥儿觉得我这位兄弟还能支持多久?”余辽见麹管家径直问他,当下却是慌了起来,他虽看得出那家仆有些处在下风,但这“支持多久”,他却实在看不出来,还没想好,就听思玉过来道:“我看撑不下五十招去。”余辽就如同溺在水中之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赶忙道:“五十,五十招罢”
麹管家看了看场中,点点头道:“也差不多,五六十招就能分出胜败了”余辽不禁看了一眼师姐,他所学武功跟思玉相差不远,但是这般眼力他却没有,心中不免又是空落落的,看了一眼自己师父。
哈哈哈,那麹管家见余辽瞅着癞和尚,笑道:“辽哥儿不必埋怨你师父,你师姐所说五十招虽然相差不远,只不过胜负却非如此,五六十招后,这位鹫神恐怕就要落败。
“什么?”
余辽和思玉顿时瞪大眼睛,仔细瞧那场中,此时那家仆比方才还狼狈,上身衣服已经褴褛不堪,双臂上也多了好几道血痕,再看那鹫神淳于中,身形比方才还快,身子滴溜溜围着那家仆转个不停,双爪挥出时已经带出嗤嗤破空之声,怎么看都不像要落败的样子。
麹管家见二人往场中一瞧,都是满面不信的样子看着自己,看了一眼靠在马车上打盹的癞和尚,缓缓道:“武学相搏,无非攻守二字。所谓攻则倾尽全力,无坚不摧,守则固若金汤,滴水不漏,学武之人莫不遵循,不过学武最忌墨守成规,若是一味的照着这个攻守之法,反倒落了武学下乘。”
“下乘?”听了麹管家这两句话,余辽还尚自在琢磨,思玉却开口问道:“那什么才是上乘”
麹管家颇为赞许看了一眼思玉道:“蕴攻于守,藏守于攻,多少有些上乘味道,不过真正高手过招,攻守之际,往往出其不意,或藏凌厉杀招于诱敌深入之处,或疾风骤雨只为求得一个********般的守势,一切攻守只可随机应变,也可说,招招都是攻,式式都是守,因此绝世高手往往出手变化莫测,变招之快,快逾闪电。一招使出,就像常人挑水劈柴一般,实则攻守兼备,只看你如何应对。你若是以平常招数抵挡,等你招数用老,他却招数立变,那时你就是想应对,只怕也来不及了。”
余辽听到这里,心中突然一动,师父平常教自己的武功,不正是一些简单的跟跳水劈柴一样的简单功夫么,想着看了师姐一眼,就见思玉也是一样眼神看着自己。两个人正思量间,就听麹管家又道:“我这位兄弟,虽然此时看起来是个守势,十招中不过一两招攻势,但却是攻敌不得不救,这位鹫神虽然看似攻势凌厉,却始终难以让我这位兄弟尽转守势,因此我这兄弟实际上是以守为攻,这位鹫神么,不得已只能以攻为守,时间一久,两人招式相熟,鹫神攻势一缓,难免出了破绽,只怕就要吃亏了。”
麹管家话音刚落,就见场中那家仆嘿然一声,往前踏出一步,双拳疾出,正是淳于中经过自己面前,身形微滞之时,这一招去势急猛,淳于中正在急转的登时顿住,双爪一分,化开那双拳来势,哪知那家仆变招突然变得极快,紧跟着双拳就如疾风暴雨一般罩住淳于中身形,淳于中一时应对不及,往后一退,那家仆贴身跟上,一步也不肯放松,淳于中原本轻灵利落的身形登时变得凝滞无比,看情形竟然是疲于招架之态。就连方才还得意洋洋的淳于和此时都看的目瞪口呆。
“破石锥!”那家仆又是一声暴喝,此时淳于中身形已然被定在场中,就见一拳当空破胸而来,正是自己退无可退,避无可避之事,当下一声冷哼,右手五指一伸一曲,力凝指尖,向前疾探,尽是要以爪对拳,破了对方拳势。就听喀拉一声,似乎是手臂断折的声音,场中两人顿时分开,那家仆看着自己皮肉外翻,露着白森森骨头的左手道:“不愧是鹫神,这凌空爪果然狠辣无比。”,淳于中却退后几步这才站住,一条右臂软软的垂在身侧,叹道:“我大哥当年想必也是输在你这一招破石锥之下罢”,
“不错”那家仆放下左手道:“只不过你大哥接我这一招时横爪当胸,因此被我劲透胸背而死。若是像阁下一般,至多也不过休养几个月,却也没有今日之事”
此时场中诸人除了第三旻这边数人之外,淳于家众人竟然不知淳于中如何落败,其中也有几个精研淳于家武学的人,深知淳于中那一爪之力,一伸一曲之间,全身功力尽数凝力手指,乃是淳于家武功绝学,敌人拳头一旦被爪力擒住,就算你拳力不衰,也只是前冲之力,那一爪后招随即一转一拧,只怕整条胳膊都要被拧脱下来,哪知却是淳于中右臂被人击断,难道那一拳前冲之力竟然有如此迅猛?几个人赶忙跑上前来,就路边拾起两根树枝,将淳于中手臂紧紧固定。眼中尽是迷茫不解之色看着淳于中。
淳于中任由几人帮自己捆扎伤臂,他如何受伤,自己心中清楚万分,自己眼见那家仆一拳送到手中,当时五指收拢,只要将对方拳头擒住,自己手臂一转,任你再迅猛的前冲之力只怕也要被卸掉一条手臂,哪知那家仆就在自己五指力道将发未发之时,紧握的拳头忽然四指弹出,紧紧并拢,自己发现不妙,想要收势已来不及,就觉得一股极大力道撞在自己手心之中,右臂随即折断,那后招自然也就发不出来,自己虽然爪力未消,也将那家仆左手伤的颇重,但对方到底只是皮肉之伤,自己却折损一条胳膊,而且对方并未乘胜进击,这一场比试,胜负不言自明。
这边淳于和见淳于中伤损一条臂膀,脸色一黑,将地上单刀一脚踢到淳于中脚下,手中铜牌一举喊道:“淳于家门下听令,今日是我淳于家报仇雪恨大好良机,我命你们即刻将这些贼子乱刀分尸!”
他这一声令下,淳于家众人都面面相觑,有些老成的,一脸轻蔑的看着他,只是不动,一些年轻的,不知道该不该听从他的号令,只是拿着兵器欲待动手,却又见旁人不动,不知道如何是好,大多数人却都看着淳于中,看他还有何话说。
淳于中看了看脚下单刀,脸上惨然一笑,附身捡起刀来,双眼一闭,就要横刀自刎,忽然觉得手中一松,急忙看时,正是那第三家家仆,他毫无防备之下,手中单刀竟然被一把夺去,就见那家仆连人带刀直扑淳于和,急忙大叫:“休要伤了我们当家”飞身赶上,那家仆一招占先,单刀舞起一阵白光,向着淳于和卷去,淳于和顿时手忙脚乱,哇哇大叫,急忙往人群中躲,那家仆冷笑道:“你这种货色也配淳于家当家?”一拳逼退几个前来相救的淳于家门人,跟着单刀一挥,用刀背打在那淳于和拿着铜牌的手腕上,淳于和当时手中失力,铜牌当时脱手飞出,那家仆单刀横摆,一溜刀光自周身掠过,就听叮当连声,几枚暗器掉落在地上,自然是淳于家中之人为相救淳于和所发,这几下兔起鹘落,极为迅捷,等到淳于中忍痛冲到跟前,那家仆已然单刀平端,刀尖点在满面恐惧之色的淳于和咽喉前,这才听见当的一声,铜牌稳稳落在单刀之上。
淳于中见自己侄子受制,登时不敢往前,沉声道:“尊驾究竟意欲如何?”那一直观战的第三旻这才道:“广平,不可鲁莽,退下罢”,那家仆听见第三旻吩咐,连单刀带那铜牌一起当啷一声扔在地上,一语不发退了回去。淳于和这时满面惊惧之色才微微褪去,伸手去拿那铜牌,不料旁边过来一人,一脚踢开他手腕道:“你既然拿不住这令牌,如何担当这一家之主?”说着将那铜牌小心翼翼的捡了起来,吹了吹上面的灰尘,走到淳于中面前单膝跪下,双手将那令牌呈上道:“请二老爷执掌家门!”淳于和顿时大怒道:“陈七,你要做甚么?我才是这淳于家家主,你这样做,难道不怕淳于家家法么?”
陈七猛然回头,怒气填膺道:“你还知道家法二字?你在风月楼睡姐儿的时候,可曾记得淳于家家法?你辜负老家主重托,寻人不见也就罢了,竟然连淮阴也不敢回,只顾得在江南风花雪月,那个时节,你可曾记得淳于家家法?你落草为寇,打劫客商,可曾记得淳于家家法?你在这大敌当前之际,口口声声只要那思玉姑娘,难道也是淳于家家法吗?你敢将淳于家家法一条一条说出来么?老家主晚来得子,对你不免溺爱,原以为你就算不成器,起码也不会胡作非为,但看你所做这桩桩件件,又何曾将这淳于家放在心上?今日若是让你执掌淳于家,只怕不出一年就要成了这江湖上的笑话!”说罢转头对着淳于中道:“请二老爷念在淳于家百年声望,念在淳于家百余门人子弟身家性命份上,执掌家门,重振门风!”霎时陈七身后淳于家人众齐齐跪了一地,齐声道:“请二老爷执掌家门,重振门风!”
“这……。。”淳于中见众人均跪在地上,一时到不知道如何是好,那边第三旻却笑道:“淳于老先生,众人之志不可违,况且你这侄儿确非执掌家门之人,你淳于家若是还想找淮南第三家给你大哥讨还个公道,只怕凭你这侄儿,有些不易罢!”
淳于中见第三旻都如此说,再看淳于家众人,都是一脸悲愤热切交集之色,沉吟片刻道:“也罢,我暂且执掌这家主令牌,待了结我大哥身死之事,再将家主之位交还,至于第三家主所说生死状之事,在下必然回去详查,若是果真有此状,淳于中定当上门谢罪,若是无有此状,淳于家舍却满门性命,也要为我大哥讨个公道。至于今日冒昧冲犯,若是第三家主心有不甘,再下和这淳于家百余口门人,定当奉陪!”淳于中话音一落,淳于家门人顿时纷纷起身,齐齐站在身后,对第三家众人怒目而视,但只第三旻要为今日之事讨个说法,即刻就要刀兵相见。只有那淳于和坐在地上,眼睁睁看着众多门人拥戴自己二叔为家主,忽然放声大哭,就地滚来滚去道:“我才是家主,我才是家主,你们这些狗贼,叛贼,逆贼……还我家主令牌来。”
他这一撒泼打滚,本来剑拔弩张的两拨人众都觉尴尬万分,淳于家人更是觉得羞愧无地,淳于中低声吩咐道:“先将他抬到后边去”,登时两个人出来,将淳于和远远拖去人群后面,就听那撒泼的哭喊之声仍旧不停,淳于中此时也无计可施,只是看着第三旻道:“今日之事,还请第三家主划下道儿来罢!”
第三旻看着淳于和被拖走之时仍旧一副无赖模样,只觉一阵可笑,脸上却不带出来,再看第三家众多家仆,个个都是一脸窃笑,顿时冷着脸扫视一圈,哪料到这一分神,自己却差一点没忍住,赶忙低头咳嗽,将那脸色变化掩饰了过去,这才抬头道:“淳于老先生多虑了,今日之事么,我意就此作罢,老先生整顿门风要紧,其次,找到那当年老当家生死状,当日之事自然也就明白,若是果真没有,第三家也必在淮南恭候!”
淳于中见第三旻如此说,脸上颜色也是变了几变,第三旻虽然并不推脱当日之事,但那“整顿门风”四字,却让淳于家人人面上汗颜,当即一拱手道:“既然如此,那么告辞了”,说完一挥手道:“回山收拾收拾,这就回淮阴去吧”,淳于家众人听得返回淮阴,顿时欢声雷动,簇拥着淳于中离去,第三旻这才吩咐众人,准备起行,就见癞和尚坐在马车上,一脸喜色,不由得问了一句道:“大和尚如何这般欢喜?莫非是佛心大发,赞叹这一场性命相搏消与无形么?”
癞和尚赶忙摇手道:“没有没有,秃驴平生最喜看戏,今日这一场戏,有文有武,有张有弛,好戏!好戏!”这话出来,众人都是一惊,连余辽和思玉都呆呆的看着自己这位从不正经的师父,这江湖上两大家刚刚消弭一场纷争,如何就说成是一场戏?岂不是是说这第三家故意布局?
果然第三旻听癞和尚如此说,刚还笑吟吟的脸上忽转阴郁,冷冷道:“大和尚何出此言?你难道疑心今日之事是我第三家在做戏么?”
“啊!”癞和尚倒是被问的一愣,见众人都是颜色犹疑的看着自己,第三家众家仆更是一派戒备神情,看着颇为愤怒的第三旻,哈哈大笑道:“浮生本就一场戏,今日之事,只索当成一出戏最好,你我都是戏中之人罢了,既然是戏,那些恩怨又何必当真?难道非要来日再续上一出,让两家杀的血流成河才肯罢手么?戏终人散,那淳于家自有他们家没唱完的戏,咱们岂不是也得启程,多少唱完给我这徒弟疗伤的这场戏么?第三家主聪慧过人,不用秃驴来点化罢?”
第三旻听癞和尚这般说,脸色当时一改肃重道:“大和尚说的是,今日之事不过一场戏,第三家并非好勇斗狠之人,若是今日果真如大和尚所说戏终人散,那恩恩怨怨,也该就此罢手了,第三旻领教了”说罢一挥手,众人重又起行。癞和尚却躺在马车前面,嘴里哼哼唧唧也不知道是什么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