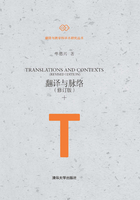
一、一则轶事/译事:米勒的期盼与忐忑
1991年10月,解构批评家米勒(J. Hillis Miller,台湾地区常译作米乐)应邀访问台湾并发表系列演讲,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是在中研院欧美所主办的第三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中发表的主题演讲《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ng Theory”)。在配合他首次访台所刊出的《跨越边界——〈中外文学〉米乐专号序》中,他提到了对即将来台访问的喜悦、期盼与不安:
我很高兴自己的一些作品现在会被人用中文来阅读;但这也使我不安。我既不懂中文,也从未访问过台湾……但是,我现在自问:“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一个我不懂的语言,在一个我从未访问过的地方被阅读时,这些作品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如何能够发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来阅读是一种奇怪的剥夺的形式(a strange form of dispossession)。我制造出来的一些东西,我的自我感受、我自己的语言、与我自己国家特定的社会及建制机构条件密切相关的一些东西,以及来自我阅读自己传统中特定作品的一些东西——这些都被拿走,而且转变成其他的东西,变成我无法阅读、知道或评价的一些东西。(米勒,1991:4)
在主题演讲中,米勒根据有关语言的践行效应(performative effects)理论,主张来自一个语言、文化脉络的理论在被译入另一个语言、文化脉络时,有些成分得以保留,其他部分可能会转变,衍生新意。他以一些具体实例说明这些转变与衍生,赋予正面评价,并称之为“新开始”(new starts)。
对于米勒来说,如果来访前的专号之翻译与编辑是“事前品味”(foretaste),那么来访后的专著之翻译与编辑则可说是“事后品味”(aftertaste)。吊诡的是,强调语言的不定与衍异、着重翻译践行与创新效应的米勒,在面对自己作品被翻译时的态度。《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一文的中、英文版经过反复修订、即将在台湾付梓之际,他在原先的结论部分增加了十几个字:
因此,理论的翻译是误译的误译,而不是对于某个权威的、明晰的原本的误译。这应该会使那些翻译理论并在新情境中以践行的方式使用理论的人高兴。“使之正确”(“getting it right”)当被视为不可能时,就不再那么迫切了,虽然那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力求正确。 (米勒,1995:26)
(米勒,1995:26)
其实该文强调的是理论经过翻译后所产生的衍异与创新,质疑原本的权威,指出“使之正确”之“不可能”及不具迫切性,但为什么在付梓之前又突然冒出了“力求正确”之说?就全文的论证而言,增加的这几个字实在难脱蛇足之嫌。然而,为什么在全文即将以原作者“无法阅读、知道或评价”的中文翻译流通时,米勒突然要加上这几个字来自我削弱、解构先前的论证?
比较合理的——或者该说,合情的——解释就是,即使是著名的解构批评家,即使在一篇讨论理论之翻译的理论性文章中(而且文章的论点在于肯定、甚或歌颂翻译在另一个语言与文化脉络中的衍生与歧异),即使译者是交往密切且具有善意、专业训练及翻译经验的同行,即使读者大多已历经后结构主义、解构批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但身为原作者/被译者的米勒,在面对自己的文章被翻译、前途未卜之际,依然会多少担心、焦虑自己的(理论性)文章在以另一种语言呈现时会遭到“误译”、误解、误读与误用,所以有此“力求正确”的吁请与期盼。 这种吁请与期盼虽与该文的立论矛盾,却属人之常情。
这种吁请与期盼虽与该文的立论矛盾,却属人之常情。
这则轶事体现了原作者与译者的微妙关系,也挑战了有关二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传统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