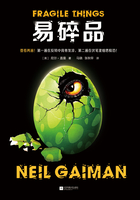
第5章 椅中的十月
椅中坐的是十月。因此眼下暮色沁凉,小树丛四周落叶飘零,红橙纷杂。他们十二个围坐在篝火边,烤肥美的香肠,品新鲜的苹果酒。油脂落在燃烧的苹果木上。香肠烤出了裂纹,发出爆响。新酒入口酸甜,浓烈刺鼻。
四月文雅地咬了一口香肠,肠衣绽开,滚烫的肉汁溅在下巴上。“啊,这尿溺的蠢物!”她说。
矮胖的三月坐在她身边,低声坏笑几声。他拿出条脏污的大手帕:“给你。”
四月擦擦嘴。“谢谢,”她说,“天杀的坏肠子烫死我了,明天怕要起疱。”
篝火那边,九月打了个呵欠:“你也太娇气了,说话改不了这腔调……”他留着一字胡,脑袋前面头发稀少,显得额头很长,睿智多谋。
“别说她,她很敏感。”五月说。她足蹬舒适的靴子,一头黑发剪得紧贴头皮,手中那支褐色小雪茄上散发着浓郁的丁香味。
“哦,拜托,饶了我吧。”九月说。
椅中的十月明白自己责任所在。他啜了口果酒,清了清喉咙,开口道:“好啊,谁先开始?”十月身下那把椅子由整块橡木雕出,以梣木、雪松和樱桃木点缀。其余十一人都坐在树桩上,整齐地绕篝火一圈。树桩表面已被漫长的岁月磨得光滑舒适。
“和时刻们玩吧?”一月说,“我坐大椅子的时候,大伙儿老跟他们玩。”
“但现在你没坐椅子,亲爱的,对不对?”九月说。要假意哄人时,他真是一把好手。
“和时刻们玩吧?”一月又说了一遍,“不能不管他们呀。”
“让那些小变态一边待着去。”四月说着,伸手掠了掠长长的金发,“我觉得,就让九月先来吧。”
九月暗自得意,点头道:“不胜荣幸。”
“等等,”二月说,“等等等等等,管事儿的还没点头呢。十月没点人,谁也别张嘴。其他人都别言语。就不能稍微懂点儿规矩吗?”这一身蓝灰色,矮小苍白的人儿不依不饶地盯着大家。
“没什么。”十月说。他长着秋日灌木般五颜六色的胡子。或深褐或亮橙或酒红的色带乱糟糟地纠结在下半张脸上,露出苹果般红彤彤的面颊。十月像一位老朋友,你从小就认识他。“九月先来,我们赶快开始吧。”
九月把最后一截香肠吞进嘴里,不失风度地嚼下去,又将杯中果酒一饮而尽。他站起来,对众人鞠躬,开口说道:
“劳伦·德莱是全西雅图最好的大厨。至少,他本人认为自家厨艺无人匹敌,餐馆门前的米其林之星就是明证。当然,此人手下功夫的确非凡,他的羊肉馅奶油蛋卷屡次获奖,烟熏鹌鹑和白松露小方饺也被《美食家》杂志誉为‘世界第十大奇迹’。不过故事要从他的酒窖说起……哈,酒窖……那才是他自信的源泉,也是他热情的摇篮。”
“对于这点敝人感同身受。大部分红葡萄在我的时段成熟,还有最后一茬白葡萄:我欣赏美酒,芬芳涌动,佳酿味醇,后韵无穷。”
“劳伦·德莱通过拍卖从私人收藏家和中间商手中买酒。每瓶酒的酿造记录他都要审过。现在黑市上名酒空瓶开价从数千到十万不等,美元英镑欧元通吃,诈骗多多,不可不防。”
“有一瓶酒,是温控酒窖中的绝顶珍藏,酿中奇品,王中之王——1902年藏拉斐红酒。在酒水单上,这瓶酒开价十二万美元。不过,真要计较起来,同类拉斐红酒全球已独此一瓶,可谓无价之宝……”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八月客气地说。十二人中数他最胖,稀稀拉拉的金发一绺绺地趴在淡粉色脑瓜上。
九月不高兴地低头瞪着邻座:“怎么?”
“这个故事是不是说……一个有钱人出钱买了这个酒,然后大厨觉得他点的餐配不上酒,给他换了一席菜,然后那富佬吃了一口,就,那什么,引起什么罕见过敏症发作,然后就死了。然后再没人喝那瓶酒了?”
九月一言不发,神色十分难看。
“这个故事你以前就说过,有些年头了。当年听着烂,现在一样烂。”八月欣然微笑。他粉白的脸蛋映着篝火闪闪发光。
九月说:“显然,对某些人来说,悲剧氛围和文化内涵不能投其所好。有的人更喜欢烤肉和啤酒,有的人则是——”
二月说:“不是我说,八月说得也有道理。我们得说新故事。”
九月扬起一边眉毛,嘴一撇。“我说完了。”他突兀地说,随即坐回树桩上。
火堆旁,十二个月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
宽厚而清雅的六月举起手,说道:“我有个故事,是说拉瓜迪亚机场透视仪操作员的。这姑娘能从屏幕上的箱包X光图像中读出行李主人的一切。有一天,她看见一幅绝美无伦的透视图,马上爱上了那名旅客。可排队的人很多,她不知道行李主人是谁。月复一月,相思之苦让她憔悴不堪。最后那人终于再次出现,她也认出他来。他是个枯瘦的老印第安人。她呢,却是个年轻黑人姑娘,二十五岁左右。她知道两人没有未来,就眼看他走了。因为男人的行李也告诉她,这个人没几天可活了。”
十月说:“好得很啊,年轻的六月,就讲这个吧。”
六月古怪地盯着他,像只受惊的小兽。“可我已经讲完了呀。”她说。
十月点点头,抢在其他人开口前说:“好,算你讲完了。”然后,他继续道:“那么,就轮到我来说吧?”
二月嗤之以鼻:“老大,顺序错啦。别人都把故事说完,才能轮到管事儿的。大轴怎么能随便搬出来呢。”
五月在格架上烤了十二个栗子,她边说话,边摆弄着栗子,排出花样来。“要是他想说,就让他说吧。”她说,“还会比红酒传奇更臭不成?快点,我还有事呢。花可不会自己开。大家都没意见吧?”
“你要搞投票?”二月说,“难以置信,难以置信!”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整把面巾纸,擦了擦额头。
七只手举了起来。四个人垂臂不动:二月,九月,一月和七月。(“不是我跟你闹情绪,”七月有些过意不去,“纯粹是为了规矩。今天破了例,以后就有借口了。”)
“就这么定了,”十月说,“故事开始前,还有人想说什么吗?”
“呃,我要说。”六月说,“有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林子里有人往这边看,我扭头去找又一个人影也没有。可我就这么觉得。”
四月说:“因为呀,你是个小疯子。”
“嗯,”九月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的四月。她很敏感,但也最残酷。[26]”
“够了。”十月说着,在椅子里伸了伸腰。他咬开颗榛子,将果肉剥出来,把碎壳扔进火里。果壳在火上嘶嘶作响,爆裂着蹦开。他开口了。
从前有个男孩,十月说,他在家里过得很苦。家里没人打他,但他就是不合拍。他和家人合不来,和镇上的人合不来,和自己的生活合不来。男孩有两个哥哥,是一对双胞胎。他们要么欺负他,要么当他不存在。镇上的人都喜欢这两个哥哥。他们踢足球,有时候一个得分高,有时候另一个进球多,轮流当场上英雄。他们的小弟弟不踢球。两人给弟弟起了个名字,叫他“小东西”。
小东西在摇篮里时他们就这么叫,一开始爸爸妈妈听了还会骂他们。
双胞胎说:“我们三个就他最小嘛,看看我们,都这么大了。”那时候,两个哥哥刚六岁,父母觉得他们很可爱。外号这种东西传得像瘟疫一样快。很快,除了不怎么认识他的人,只有祖母打电话来说生日快乐的时候才会叫他的本名“唐纳德”了。
可能名字真的是有魔力的。他就是长不大,总是一副瘦骨伶仃、紧张兮兮的小模样。打出生起他就老流鼻涕,长到十岁也没好。饭桌上,双胞胎要是碰上爱吃的,就偷他那份去分;要是东西不合胃口,他们就合计着把吃的挪到弟弟盘子里,将浪费粮食的罪状留给他。
镇上有球赛时爸爸从不缺席。比赛之后,他会给得分最多的儿子买个冰激凌作为奖励,再给得分没那么多的儿子买个冰激凌作为安慰。妈妈总说自己“在报社工作”,其实她就管卖广告位,再加征订报纸——双胞胎一长到不需要人在家照顾的年纪,她就回去工作了。
班上的男孩子都佩服他的两个哥哥。一年级头几个星期他们还叫他唐纳德,后来就被两个哥哥传染了。他又成了“小东西”。老师们基本连叫也不叫他。不过,据说私下里聚在一起时,老师们都惋惜科维家最小的孩子不如哥哥勇敢,不如哥哥机灵,没有哥哥那样好命。
小东西自己也说不好离家出走的主意是什么时候钻进脑袋里的。他更不知道白日梦怎么就成了现实。他决定离开时,车库塑料布下的储存罐里已经存了不少东西:三根玛氏巧克力条,两根银河棒,一袋坚果,一小包甘草片,一支手电,几本漫画,一袋没开的牛肉干,三十七美元(大部分都是二十五分硬币)。小东西其实不喜欢牛肉干,不过既然故事里的探险家可以接连几周只靠牛肉干吊命,这玩意儿一定不坏。他把牛肉干袋子扔进食品罐,盖子扣上时冒出“啪”的一声清响。就在这一刻,他知道,自己非走不可。
他读过些书,也看报纸和杂志。他知道出走之后可能碰上坏人,坏人会对你使坏。但他也读过童话,明白世界上也有很多善良的人。妖怪出没的地方,总有好人相助。
小东西就是这么个小东西。整十岁的小身板,有流不完的鼻涕,一脸呆板傻相。如果混进一群男孩子里,你绝对找不出他来。无论你选谁都不对,角落里那个被你一晃眼看丢了的孩子才是他。
整个九月,他把出走的日子推了又推。最后,一个特别特别恶心的星期五,两个哥哥坐在他身上欺负他,其中一个放了个屁,吵死人地狂笑起来。小东西突然觉得,无论大千世界中的怪兽有多可怕,他也一定能忍下来——说不定怪兽比起哥哥还要讨人喜欢。
周五过了是周六,两个哥哥本来该在家照顾他,但两人去镇上找他们喜欢的女孩子玩了。小东西从车库后的塑料布下面拿出储存罐,带回卧室里。他把书包里的东西都倒在床上,装进糖果、漫画、零钱和牛肉干,又用苏打水瓶子灌了些水。
小东西走进镇里,坐上巴士,凑零钱买了车票。往西去了十美元的车程以后,他见四周一片陌生景象,觉得这是个开始流浪的好地方,就跳下车步行起来。人行道已经不见了,每有汽车开过,他不得不避进路边水沟里。
太阳高悬。男孩觉得有些饿,便从包里掏出玛氏条来吃,可刚吃完又渴了。一口气灌下半瓶水以后,他突然想到自己应该省着点喝。以前他以为只要出了镇子一定满地都是清泉,可眼下一眼泉也没看见。要说河倒有一条,河上还有座挺宽的桥。
小东西在桥中间站住,低头看浑浊的河水,想起学校里教的事儿来:所有河流都要汇入大海。男孩从没见过海。他顺着河堤爬到岸边,沿水流方向走去。这里有条泥泞的小路,偶尔能看见啤酒罐和零食包装。以前也有人来过这一带,不过他一路走去时只有孤身一人。
水喝完了。
男孩很好奇人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找他,脑袋里想象出一批批警车、警犬、直升机。这些他都能躲过去。他一定能见到海。
河水流经一片岩地,卷起点点白浪。蓝鹭展开宽大的双翼,从他头顶掠过。他看见季末的蜻蜓跳起孤寂的舞,间或还有成群蠓蚊,欣然享用风和日丽的深秋时光。日近黄昏,蓝天暗淡下来,一只蝙蝠扑腾着飞落,在半空中捕食飞虫。小东西不知今晚在哪儿过夜才好。
不久小路分岔,他向远离河水的方向走去,希望能遇上人家——有空窝棚的农场也好。又走了一会儿,天更黑了,前方出现一户农舍。小东西绕着它打量起来,只见屋舍凋敝,山墙半塌,模样让人很不舒服。男孩越走越觉得,这屋子无论如何进不得。于是他翻过一道破栅栏,来到废弃的草场上,用书包当枕头,在长草间躺下身来。
男孩仰面朝天,仰望夜空,浑身衣服穿得好好的。他一丁点儿也不困。
“他们现在该想我了,”他自言自语道,“他们会着急的。”
他想象自己几年之后回到家中,沿路向门口走去,父母兄弟脸上是说不尽的喜悦。家人来接他,家人爱他……
几小时后,他醒了。皎洁的月光照在他脸上。整个世界都在他眼前,草木宛然,清晰一如白日,仿佛童谣一般。不过面前景物褪去了颜色,显得苍白冷寂。今天是满月,虽然并不完全。他想象在月球表面的阴影与沟壑间,有张脸向下看着他。月亮脸上没有他看惯了的严肃与苛责。
这时,有人说:“你是从哪儿来的?”
他坐起来,还来不及害怕,就四下看过一圈。树依旧。草依旧。“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
草场边一棵树下,什么东西动了动。他原以为那不过是树影。小东西看见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
“我离家出走啦。”小东西说。
“哇喔,”那孩子说,“你一定胆子大极了。”
小东西自豪地咧咧嘴。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想走走吗?”那孩子邀请道。
“好啊。”小东西把书包挪到一根篱笆桩下,方便稍后来找。
两人走下坡去,有意和老房子拉开一段距离。
“那儿有人住吗?”小东西问。
“不算有。”另一个孩子说。他生着纤细美丽的金发,被月光染成荧荧的白色。“很久以前有人住过,不过他们不喜欢这儿,就搬走了。然后又有人住进来。不过现在里边没人了。你叫什么名字?”
“唐纳德。”小东西说着,又加了一句,“不过大家都叫我‘小东西’。别人怎么叫你?”
男孩犹豫了一会儿。“吾爱。”他说。
“这名字好酷。”
吾爱说:“我还有其他名字,不过现在已经看不清了。”
前方有扇铁门,锈得厉害,半开半合。两人从门下挤过去,站在坡底一片小草地上。
“这地方真酷。”小东西说。
草地上有几十块大小不一的石碑,高的比孩子们整个人都大,小的刚好坐上歇脚。四周也有些碎石。小东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他一点也不害怕。这里弥漫着爱意。
“埋在这儿的都是什么人?”他问。
“大部分普普通通,还算不错,”吾爱说,“树那边以前有个镇子。后来铁路通过这里,在下个镇上修了车站。我们这儿就渐渐缩小,消失不见了。原来是镇子的地方现在都是灌木丛和大树。你可以躲进树丛,钻进老房子再跳出来。”
小东西问:“老房子都和上边那房子一样吗?”如果老房子也是那副样子,他才不想钻进去呢。
“才不。”吾爱说,“除了我老房子里没人。有时候也有动物,但小孩只有我一个。”
“明白。”小东西说。
“我们可以去房子里玩。”吾爱提议说。
“酷毙了。”小东西答道。
十月刚刚开始,夜色完美无瑕:暖如夏日,秋月当空。一切尽收眼底。
“哪一块是你的?”小东西问。
吾爱骄傲地挺起胸,拉起小东西的手,把他带到草地一角。这儿草势特别茂盛。两个孩子拨开长草,露出一块平嵌在地面上的石碑。碑上刻的日期离现在有一百多年了,大部分字迹已经蚀平,但日期下还有几个词隐约可见:
吾爱哀逝,永志不……
“我敢打赌,后面一定是个‘忘’字。”吾爱说。
“是啊,我也觉得。”小东西赞同道。
他们出了铁门,走下溪谷,来到已成废墟的老城。树在房屋间生长,建筑东倒西歪。不过一点也不吓人。他们玩了捉迷藏,又一起探险。吾爱带小东西看了些“酷毙”的地方。有座一间房的小屋,据说是全郡最古老的房子。年纪这么大的房子还能有这副模样,实在保存相当完好。
“有月亮照着我看得真清楚,”小东西说,“连屋里也明明白白的,我以前都不知道。”
“是啊,”吾爱说,“再过一阵子,就算没有月亮你也一样能看见。”
小东西有点嫉妒他。
“我想去厕所,”他问吾爱,“附近有吗?”
吾爱想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说,“我用不着上厕所。附近可能还剩几个,但也许不太安全。最好还是到林子里解决吧。”
“对,像熊一样。”小东西说。
他从后门走出去,钻进紧贴房屋山墙生长的林子,躲到树后。他从没在野外解过手,现在觉得自己像头野兽。完事后他用树叶擦了擦,走回前面来。吾爱坐在一地月光中,等着他。
“你怎么死的?”小东西问。
“我病了,”吾爱说,“肚子里直叫,难受得厉害,然后就死了。”
“如果我留下来陪你,是不是一定也要先死掉?”小东西说。
“也许吧,”吾爱说,“我猜是这么回事。”
“死是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吾爱坦承道,“没人跟你玩儿才是最讨厌的。”
“草地那儿一定有很多人,”小东西说,“他们不和你玩儿?”
“不,他们大多时候都在睡觉。就算起来了,也不爱就这么走走看看,做些事情。他们不爱搭理我。看见那棵树没有?”
九十年前大约曾是小镇广场的地方,有棵山毛榉树。光滑的树皮在岁月蹉跎中绽开裂纹。
“看见了。”小东西说。
“想爬吗?”
“这么看挺高的。”
“是啊,特别高,不过很好爬。你看我爬就知道了。”
的确如此。树身上有不少落手处,两个男孩爬在高高的山毛榉树上,像猿猴、像海盗、像勇武的战士。他们从树顶俯瞰世界。天色渐亮,东方露出一线光。
一切都在等待。夜色将尽,世界收敛呼吸,准备迎接新开始。
“我长这么大,就今天最棒。”小东西说。
“我也是,”吾爱说,“接下来你怎么办?”
“不知道。”这就是回答。
他幻想自己继续旅程,穿越了世界,终于来到海边。他幻想自己长高长大,自力更生。有一天,钱多到数不清的时候,他会回到老房子找双胞胎哥哥。他坐在漂亮的跑车里,一直开到门前。也许他会出现在球场上,友好地俯身打量他们。在他的想象里,双胞胎还是童年的身量模样。他要在城里最好的饭店请父母兄弟吃饭,家人说,他们误会他太深,待他太坏。四个人痛悔当初,痛哭流涕,他却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家人的歉意潮水般漫过他。最后,他送给每个人一件礼物,再次离开他们的生活,永不回头。
是个好梦。
其实他很明白,自己只会继续走下去,过不了两天就被找回去。回家之后一顿臭骂,一切照旧。日日夜夜,时时刻刻,他永远永远只能是个小东西。这次出走能把他们气疯,仅此而已。
“一会儿我就要睡觉了。”吾爱开始往树下爬。
小东西发现下树难于上树。因为看不见落脚处,只能探腿下去瞎寻摸。他踩滑了好几次。好在吾爱在他下面,可以动辄提醒他“向右一点”之类。两人安全着陆。
天越来越亮,月亮渐渐失去了踪影,视线反而更加模糊。两人又爬回溪谷上头。小东西老是觉得吾爱不在了,可在坡顶站起身时,他看见男孩等在那儿。
他们一路无语,走回有石碑的草地。两人一步步爬上山坡时,小东西搂着吾爱的肩。
“好吧,”吾爱说,“谢谢你来玩儿。”
“玩得真开心。”小东西回答。
“我也是。”
树林里,不知什么地方,有鸟儿啼唱。
“要是我想留下来……?”小东西突然脱口而出,但他没说完。要告别过去,机会只此一次,男孩想。否则他永远看不见海。他们不会放他走。
吾爱一言不发,良久,良久。世界是灰的。鸟声越来越多。
“我下不了手,”他终于说,“也许他们可以。”
“谁?”
“他们在那儿。”漂亮孩子指着坡上那半塌的农舍。扭曲残破的窗棂在破晓的天幕上投下黑色剪影。
小东西抖了一下:“那里有人?我以为你说里边是空的。”
“不是空的。”吾爱说,“我说里面没‘人’了,有别的东西。”他抬头看了看天,又说,“我得走啦。”他握握小东西的手,消失不见了。
小小的墓地里只剩小东西一人,清冷的空气中飘着鸟儿的歌。他向坡上走去。自己走比有人陪累多了。
男孩从篱笆桩边捡起书包,吃掉最后一根银河棒。他看着废屋,屋子也用空荡荡的窗户打量他。
里面很黑。全世界最黑的黑。
院子里杂草丛生。他吃力地拨开草,来到门廊里。木门剥落,只余小半。男孩犹豫不决,不知自己是不是在犯傻。潮湿的腐味钻入他鼻端,腐味之下另一种气息涌动。他隐约听见有东西在动,也许在屋子深处,也许在地窖,也许在阁楼,也许是拖沓的脚步,也许是乍然一跳。他说不清。
最后,他走进门去。
大家都不说话。十月说完,在木杯里加满果酒,一饮而尽。他又倒了一杯酒。
“这是个故事,”十二月说,“我觉得,只是故事罢了。”他伸手揉了揉淡蓝的双眼。篝火快熄了。
“然后怎么样了?”六月紧张地问,“他进屋了,然后呢?”
她身边,五月伸手搭在六月胳膊上:“最好别往下想。”
“还有谁有故事?”八月问,回答他的是沉默,“那么,就到此结束了。”
“总得正式宣布才算完。”二月强调。
“今天就到这里,都同意吧?”十月问过,大家齐声说好。“有人反对吗?”又是沉默。“那么,我宣布现在解散。”
众人从火边站起身来,伸着懒腰,打着呵欠,纷纷走回林间,有的孑然一身,有的三三两两。最后只留下十月和他的邻座。
“下次这椅子轮到你坐。”十月说。
“我知道。”十一月脸色苍白,生着一副薄唇。他扶十月从椅子里起身。“你的故事我全喜欢。我的故事调子都太暗。”
“我不觉得。”十月说,“只是你的夜晚更漫长,你也不太温暖罢了。”
“这么说我是好受些。”十一月说,“我想,生而为谁,是没有办法的事。”
“就是这话。”他的兄弟说道。两人牵着手,离开橘红的余烬,带着种种故事回到黑暗中去。
(谨以此文献给:雷·布拉德伯里)
(张秋早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