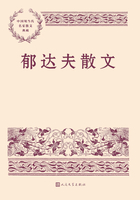
导读
谈到郁达夫,人们自然会马上想起他那惊世骇俗的《沉沦》,想起他那别具一格的小说。在“五四”的文坛上,郁达夫首先是以小说的成就奠定其地位的。但是,郁达夫同时又是一个散文大家。他的散文也戛戛独造,他在这方面的才华绽放,并不亚于小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相当大。
郁达夫许多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很难分清,如一般作为小说的《小春天气》《离散之前》等,就用散文的笔法写成,不考究人物塑造和情节构思,把它们划入散文园地也未尝不可。这大概跟郁达夫关于“自叙传”的写作主张有关。他认为散文应该比小说更带有“自叙传”色彩,只需把自己的个性表现出来就行,好的散文集让读者一看,“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1]。因此,郁达夫早期的散文,同他的小说一样,大都是直接抒写自己在黑暗社会中走投无路的遭遇和情绪,具有浓厚的“时代病”色彩,表现出与他的性格合拍的那种坦率、感伤、酣畅的风格。
如一九二二年写的《归航》,在早期散文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篇作品记述了郁达夫即将从日本回国时的复杂心情。他对于这消磨了他那“玫瑰露似的青春”的异乡天地,对于曾使他饱受“凌辱”的岛国,是那样厌恶,“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于是,就到他学习、游历过的寺院、书坊、妓家、酒店各处闲逛。作品似乎毫不讲求章法地漫然写去,与其说是以所写的异域景物吸引人,不如说是作者那种真挚、感伤的情调打动人。结尾写他看到一个秀美的中西混血少女正在船上和一个西洋胖男人谈话,不由得产生变态的、愤激的感情,万分不愿意此女子被西洋人占有。作品写道:“我恨不得拿出一把手枪来,把那同禽兽似的西洋人击杀了。”“我的心里同跪在圣女马俐亚像前面的旧教徒一样,尽在那里念这些祈祷。感伤的情怀,一时征服了我的全体,我觉得眼睛里酸热起来”。一想到在国外受尽凌辱,现在回国了,还是要受歧视,连祖国的少女也“轻侮”自己,于是越发感到“前途正黑暗得很”。整篇文章就是感伤、愤激的变态情绪的激流,难怪很容易引起当年充满青春的苦闷和弱国子民哀愁的青年的共鸣。早年写的多数散文,如《还乡记》《还乡后记》《海上通讯》《北国的微音》等等,基本上和《归航》一样,在畅述自己生活遭遇时,着重直接抒发感伤的情怀。他常常像向着朋友亲人诉苦或者拉家常那样,心里要说的,都毫无掩饰地、不拘形式地倾诉出来,使你感动。读他的散文,就如同走进他的生活,这样直率自然的写法,不但在传统散文中很少出现,在新文学中也很独特。有人曾经指责:“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调,没有!”郁达夫很不以为然地反问说:“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皮手带,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嬉笑怒骂,又何尝不可以成文章?”他似乎有意和那种堂皇而又僵死的文风对抗,以致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等文中,更直接地采用感情呼号的方式,以惊人的直率的语言,抨击现实腐恶,宣泄内心郁闷。这些散文充满生的颤动、灵的喊叫,并不注重形式,而以坦露的、自然的表达为上乘。这无疑适应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潮流,难怪道学夫子读郁达夫的作品感到被剥去衣服那样的羞恐,而渴望解放的青年却觉得这才真是在他们心琴上的鸣奏的衷肠曲。
当然,郁达夫早期散文的这些特点,也往往带来过于散漫和缺少节制的弱点。艺术是以情感为生命的,但并非情感任意发泄都可以成为艺术。这里有一个如何将生活所激发的情感进行提炼、冷却、锻造的功夫。郁达夫早年的散文稍嫌自怜过甚、情感太烈,而锻造不足。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郁达夫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更主要的是随着青春期的过去,他的思想感情比以前沉着了,散文的主调虽然仍不脱伤感,但文字却趋于深邃凝重。他少用前期那种直接的感情呼号,而注意从具体的情景细节描写去体现自己的感情,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一九二六年十月写的《一个人在途上》,就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作品。郁达夫记述了他千里之外接到儿子病危的急电,回到家里却再也见不到爱子的心情。作品捕捉了许多感伤的意象,去表现那种悲恸,如:“门上的白纸条儿”“苍茫的暮色”“衰病的她”“黝暗”中“摸走的荒路”“‘龙儿之墓’的四个红字”……这些都是极鲜明的意象,作者把悲抑的感情,浓缩晶结在这些形与色中了。接着,作者又回忆龙儿生前的一举一动,还对照着写了给孩子下殓时烧纸钱的灰烬,这些幻梦般的细节,无不糅进作者的凄楚,谁读了都感到揪心的苦痛,不禁同情作者和那些在困厄的岁月中挣扎谋生的人们。
郁达夫不但善于捕捉富于感情色彩的意象,而且善于用他那生动自然的文字出神入化地描绘出来。如《给沫若》中写到创造社的同人由于生活的压迫而不得不离散了,不久,郁达夫萎靡颓唐地回到旧日与同人们住过的屋里探看。人去楼空,“只有几根柴纵横地散在那里”,“电灯光是冰冷的——同退剩的洪水似的淡淡地凝结在空洞的厨板上,锅盖上,和几只破残的碗钵上,在这些物事背后拖着的阴影,却是很浓厚的”,“正如暴风过后的港湾一样,到处只留着些坍败倒坏的痕迹,一阵霉冷的气味,突然侵袭了我的嗅觉,我一个人不知不觉竟在那张破床床沿上失神默坐了几分钟”。你看,电灯光给人“冰冷”的感觉,好像会“凝结”在物具上;而物具疲乏地“散”在那里,仿佛沉重地“拖”着阴影……这些字眼用得真是绝妙传神,死物写活了,本来视觉中的物象,却有触觉、嗅觉上的“通感”。作者寂寞的感觉已经完全灌注并融化到具体的描写对象中,这种描写就不是客观事物简单的再现,而似乎很有感觉地向你诉说凄清。人们不能不叹服郁达夫驾驭文字的功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郁达夫将创作的重点由小说转向散文,写下大量小品、杂文和游记等。这些散文有一个鲜明的变化,就是早年那种自我表现的呼喊少了,风格转变为清丽、疏朗和隽永。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三十年代前期所写的许多游记,既保留了自己那种自然酣畅的特点,又吸取了历代山水游记中布局谋篇等方面的精华,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许多篇什都称得上现代游记文学中的绝品,直至今日仍足称楷模。
我们喜欢并肯定郁达夫的游记,主要是因为其有很高的美学价值。郁达夫像高明的画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一幅幅祖国山光水色的绝美的画卷。你看,碧水青天移动着白鹅般帆影的兰溪(《杭州小历纪程》),“半堤桃柳半堤烟”的皋亭山乡(《皋亭山》),秀美清幽中带有荒凉古意的钓台(《钓台的春昼》),怪石巉岩中极清奇的月光峰影(《雁荡山的秋月》),清逸缥缈的瀑布垂虹(《西游日录》)……祖国的奇山异水,特别是富春江一带的美好景致,在郁达夫神美的笔下,真是曲尽其妙了。
郁达夫的许多游记,原是应约为铁路局印旅行指掌而撰写的。要是出于一般的手笔,大概用艳语浓词把名胜景物、地理方位介绍形容一番也就罢了。但是读郁达夫的游记却能使人不但向往欣羡那些美景胜处,而且还仿佛由他导引,亲身游历了一番,美妙有趣的印象久不磨灭。这里有什么奥秘?仔细读来可以发现,奥秘在于郁达夫善于体物入微、渲染情韵。
凡游一处,千山万水,气象万千,不胜丰繁,但郁达夫总是以细致的观察、精微的体味,抓住某些主要景物的主要特征,探索幽微,攫取神态,写出静趣。如《钓台的春昼》写道:“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珂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作者就抓住这江山秀而且静、风景整中略散的特征,体味并指出这是一种“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这种经过深切体味的概括,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把读者的心思也点亮了。
更有的时候,郁达夫不直接去描写某种境界的特征,而让读者跟着他去体味。《半日的游程》中,郁达夫去之江山中游玩,遇上朋友,两人结伴入山,一路上说说笑笑,走过九溪十八涧,坐在溪房石条上等喝茶。两人看那“青翠还像初春似的四山”,心里“竟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只瞪目坐着,在看四周的山和脚下的水,忽而嘘朔朔朔的一声,在半天里,晴空中一只飞鹰,像霹雳似的叫过了,两山的回音,更缭绕地震动了许多时。我们两人头也不仰起来,只竖起耳朵,在静听着这鹰声的响过。回响过后,两人不期而遇的将视线凑集了拢来,更同时破颜发了一脸微笑,也同时不谋而合的叫了出来说:‘真静啊!’”这样的描写,不但使人们感到“身历其境”,而且“心历其境”;那样一种微妙的意境,不光眼睛看到了,连整个灵魂都浸沐其中了。
郁达夫别具一种生活的“吟味力”,他以自身体验乃至个性、气质去咀嚼漱涤万物,似乎可以与大自然产生情感交流。所以他笔下的景致,与其说是自然景物客观的拍照,不如说是抹上了主观色彩的风景画。他还喜欢启发读者的想象,从画幅中去体察他的感受,他的个性。当他立在五峰书院楼上,对视群山,青紫无言,“一种幽静,清新,伟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作者让你由此推想到宋儒常借幽境作讲堂,“借了自然的威力来压制人欲”的苦心,其实也是要人们体察他企图皈依自然、寻求慰藉的本意。(《方岩纪静》)而当他领着我们游天目山,人们不但为那银河落九天似的飞瀑而惊诧,而且也为游客们欢欣的心情所感染:“饥饿也忘了,疲倦也丢了,文绉绉的诗人模样做作也脱了;蹲下去,跳过来,竟大家都成了顽皮的小孩,天生的蛮种,完全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西游日录》)古人常说“揽物会心”,郁达夫可说是做到家了。
除了上述这些特点,郁达夫的游记还有许多技巧值得我们借鉴。比如,他很讲究文章的结构、布局,许多篇什(如《半日的游程》《皋亭山》《花坞》)不过千把字,但写得很有节奏,很有层次,像有经验的导游,领着你走一条曲折变幻、峰回路转的道路,一步步渐入胜境。他善于对自然景物的色彩、线形、音响作丰富的比喻和联想,细腻委婉地将自然美转化为艺术美。他的文笔力忌板滞,总是摇曳着情趣,在景物描绘中,时而引出一件掌故,时而叙几笔风俗民情,时而吟几句诗词……这一切都极和谐地编织在大自然秀美的画幅中,显得那样跌宕多姿,潇洒自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郁达夫除了写游记,还写过不少小品、杂文,其中数那些回忆文字最称佳妙。如《怀四十岁的志摩》《追怀洪雪帆先生》《光慈的晚年》《记曾孟朴先生》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构。这些文章很短,但知人论世,往往是抓住故人一些最突出的生动的个性特征,使之在字里行间跃动起来,显示出高超的人物素描功夫。在回顾往情的同时,又常常发而为抽象的概括,颇有隽永的哲理味。1938年底以后,郁达夫在南洋,还写过一百多篇鼓吹抗日的政论杂文和小品,文风变得犷放结实,其中也不乏佳作。可惜至今未有人对此作认真的研究。
信笔写来的对郁达夫散文的一点看法,当然并不足于代表他的散文成就,只是说明郁达夫不但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够得上一名家,文学史不应忽视他这一方面的成就。
温儒敏
本文节选自《略论郁达夫的散文》,《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