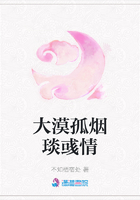
第2章 赈灾
大盛朝堂之上。
“启奏陛下,日前陛下派皇长子赴江南巡视水务,督修运河,目下沿江各郡县均奏皇长子事必躬亲,恪尽职守,每每亲自督修督建,多日来与水务官同食同寝,同居于沿江坝上,水务一应事宜进展顺利,请陛下安心。”丞相姜叱禀道。
“田祈甚安朕心,待回京复命,朕必予以嘉奖,田祯奉命整修先帝陵寝,可有进展。”
“启奏陛下,先帝陵寝已经修葺一新,二殿下也已回宫,无诏不敢上殿,现候于殿外。”太常令肖史回禀道。
“喔,宣上殿来。”
宣旨太监高呼“宣皇二子田祯上殿”。
只见殿内进来一个年轻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穿一件玄色暗花长袍,里衬素色短衣藏青曲裾,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登着玄色翘头履。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谦和有理,温润如玉。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祯儿平身,差事如何。”
“回父皇,先帝陵寝因内嵌于山崖之中,日前大雨,山石崩塌,似有毁损。但经儿臣实测,天佑我大盛,先帝陵寝未有丝毫毁坏,只是山崖中树木倾倒,儿臣已经重新栽植,另有四座陪葬陵稍有毁损,儿臣俱已修复,请父皇放心。”
“好,皇儿可堪为器,下去吧。”
“谢父皇夸奖,儿臣告退”。田祯出殿。
“大皇子殿下和二皇子殿下具是德才兼备,真乃我大盛之福啊。”姜叱说道。
“正是,天佑我大盛。”丞相一言,百官争相附和。
“启禀皇上,近日来京城涌入不少流民,大部分是从云州而来。云州今年有旱情,虽灾情不重,但还是有些百姓四处流散,是以有些来了京城。微臣求皇上恩准,以国库之粮,开些粥棚,让这些流民度日,旱情过了,他们自会返乡。如若放任自流,恐会有老弱病饿而亡,还请皇上明鉴。”
“皇上,老臣以为流民应导,不应堵,只要令其口中有食,便不会生事。大皇子殿下近日便会返回京城,不如就令其主持粥棚之事,大皇子必堪此任。”丞相姜叱言到。
“启禀皇上,微臣以为,二皇子殿下目下即在京城,不如令二皇子殿下主持此时。”
朝上争论不休。
“好了,开粥棚之事繁琐,待再议。”
永泰宫。
“儿臣给母后请安。”
“快起来,坐,皇儿今日退朝甚早,怎么,朝上无事么?”
“无甚大事,田祈和田祯,差事办得不错,儿臣也轻省不少。今日朝堂之上,朝臣皆赞。只是有一事,儿臣想来请母后示下。”
“何事?”
“近日京城涌来不少灾民,朝臣皆上书,开粥棚赈济。然开粥棚之事,由田祈主持,还是由田祯主持,争论不休。”
“嗯,祈儿和祯儿都长大了,这些个站朝堂的老家伙,心里有了盘算。依哀家看,皇子还当以学业为重。”
“儿臣也以为是,只是这赈济之事,乃当务之急,儿臣一时没有人选。”
“哀家向皇儿举荐一人,”宣裕太后顿了一顿,说:“含元郡主。”
“阿婧?”
“正是。赈济灾民一事,非朝廷公务,只为应对灾情偶一为之,是以皇上安排各府司,不合宜;开内廷皇家府库,最适宜便是安排皇室中人主持,皇子不适宜,礽儿又太小,阿婧最合适,她身为女子,纵使在百姓中搏些贤明,也无妨。况这丫头有几分聪明,定能办好这差事。”
光合帝略一思索:“便依母后所言,此事还请母后下道懿旨。”
“好,皇儿静候佳音便是。”
“如此,儿臣告退。”
光合帝走后,姜琰从内室出来。
“祖母。”
“阿婧,过来,祖母与你有话说。”无人在侧之时,宣裕太后与姜琰,当真如寻常祖孙一般。
“祖母有何吩咐。”
“阿婧,祖母派你个差事,你可愿意?”
“能为祖母分忧,阿婧自然愿意,祖母尽管吩咐。”
“尽日京城有不少云州来的灾民,皇上要开内府赈济,祖母想交由你来主持,可好。”
“甚好,祖母当真知阿婧脾性,阿婧正愁每日闷在宫中无事呢。阿婧愿尽全力,前日阿婧回家看望父母,也见到一些灾民,属实可怜。”
“嗯,那祖母问你,你想如何为之?若是不得要领,祖母可不敢放了你这差事。”
“祖母,阿婧私以为,单皇家府库恐不足,且一旦开了粥棚,恐还会有灾民涌来,如若准备不足,恐有民变。因此上,阿婧想联合京城各家的贵女,让她们都开自家粮仓,赈济灾民,您看如何?”
“嗯,这倒是好法子。不过那些个权贵家的小姐们,终日只知玩乐,会愿意出钱出力赈济灾民么?”
“祖母不知,如今那些权贵家里的小姐,皆以阿婧为榜样。阿婧穿了什么,戴了什么,做了什么,她们都竞相效仿。这次赈灾,阿婧若主持,必能搏得贤名,她们怎舍得让我一人独占鳌头。更何况开几个粥棚,对于她们来说,只是几套衣裙,几件首饰罢了,阿婧必可说服她们。另外,阿婧会把粥棚开在京城外西郊,这样不出一两日,京城的流民,就都会出城集中到西郊外,这样,京城内城流民之忧可解。阿婧还会请大夫在西郊,医治生病的灾民,再熬煮去瘟茶。灾民远道而来,难免会有瘟毒,要防瘟疫在京城流行。至于需要多少钱米,目下阿婧不知灾民之数,也无法估算,但阿婧想,京城及京城周边大镇所储粮米,应足够应付,如若当真有缺,便从南边调度即可;另外抗瘟疫的药材,京城六家最大的医馆药铺,这种寻常药材必定充足,不必担忧;至于人手,就更好解决,各家出家丁厨娘管顾粥棚,再调京畿营军士外围把守即可。”姜琰一口气说完,宣裕太后定定看着姜琰。
“祖母,您怎么不说话,是阿婧说错了么?还请祖母教导阿婧。”
“阿婧,你说的好,便依你所言,放手去做吧。”
“真的?阿婧多谢祖母,那阿婧去了。”
京城西郊。
粥棚已开了一月余,各家权贵小姐,全都失了兴致,只有姜琰,依旧顶着烈日,着了男装,扮作寻常富户公子,在西郊忙碌。
“公子,这粥棚开了一个多月了,好多灾民都已返乡了,奴婢看不出几日,这粥棚便可撤去,日日都来看顾,连奴婢都受不了,公子怎么能吃得消?奴婢看,公子这些时日都累瘦了,也晒黑了许多。”
“无妨,本公子不在意这些,碧茵,几日前那个重病的灾民,如何了?”
“回公子,张大夫说今晨清醒了半刻,后又昏睡。”
“走,去瞧瞧。”
姜琰带着碧茵,走进一处宅院,一间厢房中,一男子昏睡在榻上。姜琰轻声进房,问道:“张大夫,这男子如何?”
“回禀公子,他是一路饥冷,着了风寒,高热不退,引致昏迷。多亏了公子的那些名贵药材,昨夜高烧已退,性命已无虞。今晨醒来,进了些米汤,应无大碍,休养几日,便会康复。公子真是仁厚,那些药材价值百金,用在一个灾民身上……”
“张大夫,药材再贵重也好,终是要救人性命,方是其所。”
“是是是,公子所言极是。”
“公子,他醒了。”碧茵叫到。
姜琰走到榻边,看到男子果然转醒,便道:“先生终于醒了,我便可安心了,先生莫要多虑,尽在此处休养,待痊愈后再计。”
“公子,在下吕护,适才都听见了,先谢过公子的救命之恩,大恩大德,吕护永生不忘。”
“莫要多言,他事日后再说。”说完便转回身对碧茵道:“碧茵,跟我出来。”
说完便带着碧茵离开。
“碧茵,这片大宅院我已经买下来了,你着些人把屋子修整一下。”
“啊,公子,这些破屋,您买下作甚?”
“天气渐凉,将那些未返乡的灾民,暂且安置在这些宅院里。”
“啊?还要安置他们,那不是还要经常来?”
“正是,还有,以后只要来这里,不许叫我郡主,记住了?”
“记住了。”
又过了半月,粥棚尽数撤去,姜琰将无处安身的灾民,尽皆安置在西郊大宅中,每日供应米粮,隔三五日,姜琰便换了男装,带着碧茵前去探看。
这日姜琰刚进大宅,迎面走来一年青男子,见到姜琰,施礼道:
“见过公子。”
“不必多礼,你是吕先生?”
“正是在下。”
“吕先生,进房详叙。”姜琰边说,边进了厢房,吕护也跟了进来,二人在案前坐定。
“公子,吕护再谢您救命之恩。”
“吕先生不必言谢,路见不平,亦要拔刀相助,更况是人命呼?任是谁也不能罔顾。”
“公子大义,不以此事为意,但在下必铭记于心。”
“此事不提,吕先生言谈,不似一般灾民,未知因何事一路困顿,流离至京城。”
“公子明鉴,在下是云州人士,以经商维生,家中只有老母。云州旱灾之前,在下正在江南,急忙赶回家中,老母却随乡里人出来乞讨求生。在下便一路寻找老母,及至到了京城,终于找到同乡,才知老母已在途中病亡,在下伤心欲绝,一病倒了,幸得公子相救。”
“原来如此。那吕先生意欲何往,若要回乡,可取些银钱去。”
“呃,”吕护略一思索,“如此,在下告罪,想讨一溢金。”
“好,待我吩咐小子备下。”
“公子,在下还想请教一事,那些京城贵女,开了粥棚,搏了贤名便去了,不再理会灾民是去是留,公子为何要暗地里将这些病弱灾民安置于此呢?”
“这些灾民多为老者幼儿,他们若是强行返乡,恐路上就会病饿而死。流落在京城,恐也性命堪忧,我岂能见死不救?暂且安置此处吧,余事再议。”
“如此,公子是不打算将这些灾民遣散回乡了?”
“若有欲回乡者,我不阻拦,再赠些盘缠,若不欲回乡,便在此处,我断不会强行遣散,这京城西郊外的一片宅子,我已买下。”
听姜琰如此说,吕护站起身,作揖道:“公子仁心,吕护替云州灾民谢过公子,吕护这便告辞了。”说毕便出了房间。姜琰亦出房门,吩咐碧茵拿了金子给吕护,吕护便离了大宅,不见踪影。
“公子,这人是讹诈啊,回家乡需要一溢金子做盘缠?”
“莫如此说,这吕先生不是宵小之辈,必有他用,无需多虑。”姜琰见吕护离开,也不多想,只去各处探看。
大盛皇城永泰宫。
“孙儿拜见太后。”
“免礼,婧儿,过来祖母这里。”
姜琰趋步来至宣裕太后榻前,坐在矮凳上,手搭上宣裕太后双腿。
“婧儿,这两月来你日日不在宫中,真是心野的很,放你出去,你便不记得祖母了。”
“祖母,怎会?阿婧是怕差事办不好,惹祖母烦心,是以不畏辛苦,日日都守在西郊,如今粥棚已撤去,灾民也尽数回乡,阿婧回来向祖母复命,请祖母教导阿婧,可有何疏漏之处。”
“嗯,祖母都知道,阿婧做得很好,祖母没有什么可教导你的。快让祖母看看,阿婧都晒黑了,也瘦了些。”
“无妨,祖母,婧儿不在意这些。婧儿差事办得好,想向祖母讨赏。”
“哦?这小丫头,做了一点点事就要赏,你即如此说,想是有了打算,说说,想要什么?”
“婧儿想要长生不老的祖母,求您赏赐。”
“哈哈,你这丫头,又胡说,这世上哪有长生之人啊。”
“不,婧儿不依,婧儿就是要您长生不老。”
“好好,那祖母就依你。”说着,宣裕太后慈爱的搂住姜琰。
“婧儿,你时常同京城中的贵女,公子们相见么?”
“嗯,一月中总有一两次,婧儿出宫回家的时候,他们经常来邀约,有时婧儿也会相邀。”
“那你们在一处都做甚。”
“无非是赏花,品茗,吟诗作赋。”
“那你们都聊些甚事?”
“除了穿戴首饰这些不相干的,她们这些权贵家的小姐,最喜欢打探祈哥哥和祯哥哥的消息了。”
“哦?那你都如何答复。”
“婧儿只捡些无关痛痒之事,胡乱支应,内廷之事怎可随意透露。”
“嗯,婧儿有分寸。”
“自然,是祖母多年来教导有方。”
“婧儿,再有人同你说起你大哥二哥,你便多多夸奖,说皇上近来常考问他三人的功课,黄老之道尤甚。”宣裕太后说完,便微笑着看着姜琰。
姜琰略一思索,便说:“婧儿明白了,婧儿自会不着痕迹的传出去,这些贵女有甚回应,婧儿也会回来禀报祖母。”
“还有,旁人无妨,王家的小姐一定要请。”
“王家?是安国公王素的嫡女王珩,她的父亲常年镇守西南,她的叔父王凤任御史大夫,祖母放心,阿婧明白了。”
“嗯,婧儿聪慧,此事莫要说与他人。”
“是,祖母。”
是日姜琰出宫回到丞相府,便亲自写了帖子,请了郭家的小姐,即当今皇后的堂侄女郭蓉,齐家的小姐齐惠,于家的小姐于晴,卫家的小姐卫薇,王家的小姐王珩,及许家、张家等几家的小姐,翌日一同至东市铜雀楼旁,姜琰的私宅品茗。着管家去各家送了帖子,又着碧茵头一日便过去准备。
第二日,姜琰为主,一早便来至府中。姜琰的这座私宅,平日里无人来访,只用于姜琰招待京城贵女与公子,虽比丞相府小了大半,但亭台楼阁,奇珍异兽,也是应有尽有,颇有些别出心裁之处,是以年轻小姐与公子们,多喜此处。
“郡主,具已安排妥当,郡主可要去瞧瞧?”碧茵来房中报。
“不必,你安置便好,着人去门口迎候。”
“是,郡主,已安排人去候着了。”
姜琰在花厅中迎客,不一时,各家的小姐具已到来,落座于花厅。
“各位小姐,欢迎大驾光临寒舍,先喝杯茶。”
“郡主今日清闲,有雅致相邀我等。”是齐家的小姐齐惠,齐惠活泼开朗,再加齐惠的堂姐,是姜琰之嫂,因此与姜琰更熟络。
“粥棚赈济灾民之事,多谢各位小姐慷慨,太后她老人家夸赞各位呢,因此上今日相邀,一来致谢,二来秋高赏菊品茗,最是风雅。”
“郡主不必客气,不过举手之劳。”
“说起太后,郡主连日来忙着粥棚,未能侍奉太后,太后跟前只剩三皇子殿下承欢了。”王家的小姐王珩说道。
“三皇子殿下如今也不能日日侍奉太后了,昨日太后见了我还说,孩子大了,留不住了,如今只剩文华公主,三皇子殿下如今也同大殿下、二殿下一同读书了,近两月来皇上功课问的紧,他们三人都不得闲,我也好久没见到三殿下了。若不是皇上要他们好好用功功课,那这开粥棚的差事断断落不到我头上。”
“三位殿下天资聪颖,功课又有何难,想必是皇上给三位殿下加了新的功课。”
“无甚新功课,我悄悄去文昌阁瞧过,左不过是‘不尚贤使民不争’,我大盛崇尚黄老,此为国术。”
“原来如此。”王珩听了,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