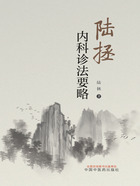
第一节 中医药的起源
中医药的起源,是人类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过程的认识,它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的生产和医疗实践。
我们不从远古说起,那都是地下发掘考古文物史料。现就从先秦时期开始,以书为证,以大系为主线,简述史略。首推《黄帝内经》的出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其中《黄帝内经》九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黄帝内经》是为仅存者。此外,还有许多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古代医术,例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简帛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及《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这些简帛医书都是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下葬的。据有关学者认为,各书的编撰年代并不一致,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最晚的乃是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所成之书,其中尤以《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最为古朴,是现今已知最早记载经脉学说的中医文献。《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所述十二经脉,正是在帛书所述十一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知,在《内经》成书之前,曾有过更为古老的医药文献。在《内经》中亦有引用记载古医书二十一种(见于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单是《素问·病能论》篇提到的古医书就有《上经》《下经》《金匮》《揆度》《奇恒》等多种。这些已佚的古代医学文献,还可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某些内容相互印证。
《黄帝内经》即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成书时期和著撰者,非出于一时期一人之手,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充实于秦汉时期,由众多医家搜集、整理、综合而成,甚至包括东汉乃至隋唐时期,不断修订和补充。
《素问》和《灵枢》,原书各九卷,每卷九篇,各为八十一篇,合而为一百六十二篇。《素问》流传到唐代只存八卷,其中第七卷的九篇已佚。唐代王冰注解此书时,又称从其师元珠先生处得到《素问》“旧藏之卷”的秘本,便补充了《天元纪大论》等七篇,仍缺两篇。现存《素问》,虽有八十一篇的篇目,但其中的第七十二篇《刺法论》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论》,只有篇名,而无具体内容。直到宋代,又补充了两篇,附录于该书之后,称为“素问遗篇”,显系后人伪托之作。
《灵枢》一书,原来只剩残本,北宋元祐八年(1093),高丽献来《黄帝针经》,哲宗随即下诏颁发天下各地。(可见于《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元祐八年正月庚子,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后至南宋的史崧,才把“家藏旧本《灵枢》”加以校正出版,这就是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
从现在的《素问》《灵枢》两书来看,各篇篇幅长短悬殊,文字风格体例亦不一致。例如《素问·经络论》通篇仅一百四十多字,而该书的“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篇,字数却在六千以上。又如《灵枢·经脉》,字数有四千五百多,而同书的“背腧”篇,仅有一百四十六字。在文字风格上,有的很古朴,有的又类似于汉赋,有的所举事例是汉以后才出现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阐述养生时,有些语句颇像《老子》;《素问·宝命全形论》称民众为“黔首”,当是秦或秦以前的称谓;《素问·生气通天论》言平旦,言日中,言日西,而不以地支名时,似为秦人所作;《素问·脉解》言“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则可断定属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以后的作品;因为秦代和汉初皆用颛顼历,而颛顼历是以亥月为岁首,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才改为以寅月为岁首。从多篇的内容来看,有的还有互相解释的关系。如《素问·针解》和《灵枢·小针解》是解释《灵枢·九针十二原》的,这就表明《针解》和《小针解》是在《九针十二原》之后所成的。由此可见,《内经》之书,确非一时一人所撰成。
《内经》的基本内容和成就,可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疾病预防等。《素问》所论范围,有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及针灸等。《灵枢》内容亦大致相同,除了阐述脏腑、病因、病机外,还着重介绍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两书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阐发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辨证论治原则,体现了人体与外界条件统一的整体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对药物学的认知有了新的进展,见于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多。西汉初期有过药物专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到古代医药书中有《药论》,可惜已经失传。在《黄帝内经》中记载了十多个药方,其中提到了泽泻、半夏、连翘等多种药物。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医书《五十二病方》,虽非药物专著,却记载了黄芩、芍药、黄芪、甘草、蜀椒等药物243种。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西域的红花、葡萄、胡桃、胡麻、大蒜、苜蓿及其他道地药材不断输入内地。《神农本草经》的出现,说明药学有了较快的发展。对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有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有认为成书于东汉时代。多数医家认为,《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本草经》)亦和《内经》一样,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大都是秦汉以来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和发掘,直至东汉时才整理成书。《神农本草经》之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其书始载于梁代阮孝绪的《七录》,《隋书·经籍志》亦作了著录,但均未说明写作年代和作者姓名。郑玄认为乃神农氏所作,皇甫谧认为是岐伯和伊尹所作,这显然是不可信的。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说:“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以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又说:“本草时月,皆在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颜氏家训》亦云:“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由后人所掺。”陶弘景和颜之推都指出,《神农本草经》所记药物产地,多为后汉时所设置的郡县,因此可推断本书为后汉时所作。陶弘景还根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再根据书中有较多的“久服神仙不死”等语的情况来看,此书受东汉道教思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陶氏之说不无道理。
关于本书的作者,陶氏所说可能出于张仲景、华元化之手,这只是一种推测,其说不太可靠。该书何以称“本草经”?因古代是以植物药为主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药,治病之草也。”五代时韩保昇亦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至于书名,关于冠以“神农”,一是为古代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二是一种托古之风的反映,就像《内经》之前冠以“黄帝”之名一样。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神农本草经》原书早已失传(一说在唐代初年就失传了)。现今所流传者,都是后人从宋代《证类本草》及明代《本草纲目》等书中辑佚所成。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和成就,全书共三卷(亦有作为四卷),收载药物365种,分上、中、下三品,其中上、中品各120种,下品125种。上品之药,多属补养类药物;中品之药,为补调兼顾治病之药物;下品之药,为除病攻邪之药物。在药物理论方面,以序例之总论形式提出了药有君臣佐使、阴阳配合、七情和合、五味四气等药物学理论,并介绍了药物的别名、性味、生长环境及功用、主治等。本书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亦可说本书是奠定了中药防治疾病的基石。
《神农本草经》从记载内容和内涵底蕴来看,集东汉以前药物学之大成,亦是我国现今最早的药物典籍,通过系统总结秦汉以来的医家和民间医的用药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魏晋以后历代诸家的本草学,都是在该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中所述药物学理论,包括药物性能、功效及加工炮制方法等,至今尚有一部分内容仍有参考价值。所以本书仍然是学习中医药重要的参考书,但是限于当时科学水平,书中亦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缺点和错误,由于东汉时期谶纬神学盛行,因此书中也掺杂了一些神仙道教思想内容。例如“水银……久服神仙不死”“泽泻……久服不饥,延年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紫苏……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等。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医学理论逐渐完善。在《内经》理论的建立和《本草经》药物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医学初具规模。但临床缺乏诊病治疗方法。东汉张仲景(约150—219),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一说今南阳市)人。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建立了临床医学体系,诊疗疾病的水平得到了飞跃发展。《伤寒杂病论》实际上讲的是两大类疾病:以外感伤寒为主的疾病,以内伤杂病为主的疾病。外感伤寒以六经论治,内伤杂病以脏腑论治。张仲景还提出了以理法方药为主的辨证论治原则。论述外感伤寒的部分即今之《伤寒论》,论述内伤杂病的部分即今之《金匮要略》。伤寒为病,大都以外感病邪所致,病变传递多以先表后里,先实后虚,先热后寒,先阳后阴。内伤杂病为患,大都气血亏损,脏腑受伤,再以痰湿瘀毒内阻,诸病渐成。同时,《金匮要略》兼及妇科病和外科痈疽肠痈,其辨治精神与《伤寒论》基本一致,但《伤寒论》先明列伤寒等疾病,再以六经分证论治,而《金匮要略》不以独立疾病而以脏腑病证辨证分治,故适用于杂病论治。《金匮要略》分类明确,辨证切要,对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的论述均甚精当。在病因分析、归纳方面,其指出了三因致病学说,“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事、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为中医学的病因学说做出了一定贡献,在诊断和治疗上亦总结了不少可贵经验。
从《伤寒杂病论》来看,实际上已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下、吐、和、清、温、补、消等八法。
同时,《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亦有贡献。《内经》方剂甚少,仅有10余首,到了《伤寒论》时载方就有113首(实为112首,因为其中的禹余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首,丰富了临床方剂应用。
嗣后,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医学不断地进步与完善,到了晋代出现了脉学专著。王叔和撰成《脉经》,指出了脉诊的重要性和难以掌握性,他在自序中说:“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辗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况有数候俱见,异病同脉者乎。”同时,王叔和指出脉学必须理论结合实际,四诊合参,“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赅备”。
《脉经》首先确立了寸口脉法,分寸、关、尺三部脉位,配合脏腑,联系寸口切脉,倡导了临床广泛应用的独取寸口诊脉法。
到了隋代,巢元方系统地总结了中医病因、病理、证候学,撰写《诸病源候论》,在病源与症状、证候理论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全书共50卷,分列67门,论述1739种病候,概括人体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病变,可称收罗最广,叙证最多,内容极为丰富,是总结了魏晋以来的临床证候大全。本书对病源与证候研究既广泛又详细,所列病类,有中风、风湿痹、虚劳、伤寒、天花、霍乱、疟疾、痢疾、水肿、黄疸、消渴、脚气、呕哕、痔漏、痈疽等,以内科为主,包括外、儿、妇产、五官、神经精神等多科疾病的内容。如妇产科又分为妇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五类等。说明1400多年前,中国医家对这些疾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对病源的认识上,除根据传统的医学理论对病源进行解释外,还根据临床表现,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如“温病候”中,认为某些传染病是由外界有害物质因素“乖戾之气”所引起的,这些物质还能“多相染易”,并且可以服药预防。对某些病源的认识颇具真实性。例如关于寄生虫病的感染,明确指出疥疮中“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又说患寸白虫(绦虫)病,是因吃了不熟的牛肉所致。对“漆疮候”,认为“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说明对本病的发生,已认识到与人的体质禀赋有关。同时本书对某些疾病如糖尿病、脚气病、麻风病等症状的描述亦颇准确。并指出:“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多发痈疽。”又说:“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虫所缘……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疼痛,或缓纵不随,或挛急……或有物如指,发于腓肠,径上冲心,气上者,或胸心冲悸。”又说:“凡癞病……初觉皮肤不仁,或淫淫苦痒为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轸辄赤黑……令人顽痹,或汗不流泄……身体遍痒,搔之生疮……顽如钱大,锥刺不痛……眉睫坠落……鼻柱崩倒……从头面即起为疱肉,如桃核小枣。”同时书中又提及“妊娠欲去胎候”“金疮肠断候”“拔齿损候”等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已有施行人工流产、肠吻合及拔牙等手术,可惜没有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