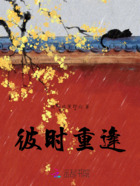
第7章 采花和挖笋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公园中心此刻南城孤儿院的少年合唱团正在排练曲子。
稚嫩的声线配上欢快的节奏,小提琴的音色轻盈灵动,歌声随着花香在人心间泛起层层波澜。
漫天梨花,一片雪白,仿佛置身在冬季。
蜜蜂翩翩飞舞,嗡鸣声让人不敢靠近。
“有点想吃梨子了。”刘雪灵提着小花筐,把下巴撑在吴明慧肩膀上。
“那你望花止渴咯。”吴明慧被逗笑,无奈的摆手。
刘雪灵站直身子蔫巴道,“这种时候你不应该说,‘想吃多少我给你买’吗?”
纤细的手指带着剪刀在花海中游走,枝丫上洁白的梨花沾上薄薄的水珠,随着风、手指碰撞低垂,娇俏动人,芬香扑鼻。
“没人能违背自然规律,所以我很难说出这句话。”吴明慧说。
刘雪灵微不可察的叹气,抬起头看向破晓的天空,“今天的天气真不好。”
“不好的话,还吃梨花饼吗?”吴明慧笑笑。
这其实不是反问句,就算自己真说不吃了,家里那几位可能会把她扛到天台吹一晚上的风,然后再熬一壶苦涩的姜汁给她。
她想想就觉得毛骨悚然。
怎么大家都学会了吴明慧的手段。
“吃,这一篮还可以泡两坛梨花醉。”刘雪灵继续补充,“我记得家里还有一坛未开封的梅子酒,算算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能喝了吗?”
说完,刘雪灵眨起星星眼,一脸期待的看着她。
吴明慧想,这人明明酒量一般,酒品也算不上好,怎么就变成酒蒙子了呢?
不过她没拒绝,“可以,公园入口左走到头,有几棵桃树,花开得很红,也可以摘一些。”
“好诶好诶。”刘雪灵欣喜的说。
摘梨花算不上精细活,至少对刘雪灵而言是这样的。
于是她百无聊赖的打量起四周来。
就着春意和暖阳,不少人围在岸边的亭中,或品茗或对弈,更远一点的还有孩童在放风筝。
真称得上其乐融融。
连她自己都未察觉,嘴角泛起的笑意。
吴明慧揉着酸痛的脖颈,打了个哈欠,转头一看,就问,“笑什么呢?”
“啊?”刘雪灵吓了一跳,“有吗?我在想每天都是这样的日子就好了。”
吴明慧低声笑笑,正要开口,就眼尖的看见正前方亭子中坐着的人,一顿,往刘雪灵靠了靠,“你看,那是不是安琴呢?”
刘雪灵凑了上来,“哪呢哪呢?”
说话间,两人竟然不知不觉往前走了上去,等走到面前时才顿觉冒昧。
两人对视,都在对方眼睛里看到了惊恐。
怎么一下子就走上前来了?
叶扶摇手执黑棋正落下,一抬头就看见站在张安琴身后脸上写着心虚的两人,轻咳两声忍住没笑。
张安琴不疑有他,思索片刻后才落下白棋,有些懊恼,“看样子这局我又要输了。”
听了这话,刘雪灵探头出来看了看,一时也并未说话。
满是梨花的小花筐被吴明慧放到左手边,她吹了吹落在圆凳上的花瓣,然后落座。
张安琴一时愣住,看清人后惊喜的问,“阿慧,雪灵你们也在这啊?”
刘雪灵顺势也坐下,单手撑着头,“你今天这身真衬人。”毫不掩饰夸奖的话对她说。
张安琴有些内敛,一下红了脸。
“扶摇姐,打扰啦。”吴明慧冲着叶扶摇甜笑的打招呼。
“哪里打扰,今日天气好特意约了阿琴来闲耍。”叶扶摇“唰”一下扇起扇子,“聊聊家常,你们呢?”
吴明慧点点头,从花筐里取出朵花来,“摘些梨花,回去做饼。”
叶扶摇若有所思,“你们这两年都做,真的不腻吗?”
刘雪灵接话反驳,“可是都只吃一次诶。”
张安琴问:“怎么没叫我呀?”
吴明慧:“今天周末,能多休息就多休息,再说你晚些总要过去的。”
叶扶摇:“那有没有我的份啊?”
吴明慧:“当然了,就看扶摇姐去不去赏光啦。”
叶扶摇捻起黑棋在手,“嘴那么甜,今早吃蜂蜜了?”
一子落下,胜负已分。
张安琴倒是松了口气,“下次让我两颗呗?”讨好似的冲叶扶摇说。
“半颗都不行哦。”叶扶摇头,“你的棋艺落下很多了,再不追上来罚抄‘忘忧清乐’十遍。”
张安琴被震慑住了,苦着张脸,“最近忙了一些,我保证下次肯定能看到进步。”
叶扶摇勉强点头。
她和张安琴的关系,亦师亦友。那年她刚来上海打拼,进了张家名下的店铺,寻了个洒扫的活计,工钱不多,但供她个人开支也绰绰有余。遇见张安琴的时候,算是她平生最狼狈的样子。
来店里买东西的客人是那一片臭名远扬的恶霸,肥头大耳油光满面,上来要碰她,她给了那人一巴掌,男人怒火中烧把她拉到后院,按进水缸里,扯掉了她的上衣,边打边骂,可周围没一个人敢上来。
她力竭绝望之际,想着不如拔了她头上的簪子和他同归于尽算了。
这时张安琴出现了,跟从天而降似的。
张安琴身子瘦弱,那年也才不过17,被男人推得撞上木桩,头破血流,掌柜见状才上来阻拦。和张安琴同路的是她的弟弟,跟她一向很亲,没几下就给男人按在地上,交到了警察署。
这是她们的初遇,算不上美好。
此后张安琴给她安排了新的活计——小学堂的女老师。
是件足够指着脊梁骨咒骂的工作。
她反倒很坦然的接受了。
叶扶摇问过她为什么,张安琴反问“那你为什么敢接?”
她说,因为我的名字,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几人没有闲聊多久,因为叶扶摇临时有事先行离开,在小亭之中下了三局棋后,又重新返回花海中去。
“怪不得韩大家会说‘最是一年春好处’,我真巴不得这样的场景时时存在。”把玩手中的桃花,刘雪灵感叹到。
“雪姐姐是不是太贪心了,哈哈哈。”张安琴放开桃花的一段枝丫,调笑说。
“好好提着你的花篮吧,免得等会撒一地。”吴明慧一同打趣。
“糟,你们谁拿的背篓?”看着散落在地的春笋和破了个大口的背篓,许国平痛心疾首。
张铃悦左瞧瞧右看看,不说话,吴叶上望望下瞅瞅,也不说话。
许国平以手扶额,没眼看两人心虚的脸。
无奈的把锄头扔到一边,解下身上的围裙铺在地上,把一个个沾泥的笋子包起来,“还好挖得不多,不然就难抱了。”
听话的两人连忙上前来,有样学样的解下围裙。
“谁知道这背篓那么脆,我明明记得上次用还好好的呀。”吴叶擦掉手上的泥,不解疑惑。
“你要不要再想想,上次用它是什么时候了?”许国平皮笑肉不笑。
“!”张铃悦想起来了,至少要追溯到两个月前,她们背着它去菜地里拔萝卜。
“怪不得,当时谁说它下面松了来着。”还没擦干净的手搓搓鼻子,吴叶冥思苦想半天,“呀,是我,可是我们不是回家就给补了吗?”
许国平:“补了吗?”
张铃悦顺势:“补了吗?”
吴叶:“......”
吴叶想不起来了,她只隐约记得拔完萝卜那天她们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连饭都没吃上。
之后又连着吃了一个月的萝卜,以至于过年那天,她看到饭桌上的萝卜差点拔腿出门。
“如果早上没那么急,带把柴刀出门都还可以补一补。”许国平叹了口气,“现在这荒山野岭的,你们两个把我拐去卖了都不会有人知道。”
张铃悦立马伸出食指堵住了她这话,“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她左右看了看,“不行就扯几根藤来编成大网,铺在下面。”
许国平:“我的大会长,且不说编出来的能不能用,就以那些藤蔓的数量和质量还不如我们抱着回去。”
张铃悦:“好吧。”
“那只能重新分工了,我和夕颜把这些抱到车里去,阿许再挖一些?”吴叶提议。
“好,你们小心脚下的石子,上面的露水还没干透。”把手上东西递给张铃悦,从地上捡起锄头,许国平嘱咐。
“你别像刚刚那样差点砸到手就谢天谢地。”张铃悦逗趣的笑了笑。
春天的笋子有两种类型,一般分为土中笋和冒尖笋。
土中笋一般立春之后就会从根部发芽,埋藏在泥土里,笋体较为肥壮,外壳多为褐色或者黄褐色,带有细小斑点和绒毛,笋尖鲜嫩,颜色较浅。由于较少接触外界环境,味道相对较淡,苦涩味轻,质地细腻,水分充足,吃起来软糯。适合用于炖、焖的长时间烹饪的方式,炖煮之后,能吸收更多汤汁的味道,变得香浓入味。
因为是根部发芽,挖笋就比较讲究:
将笋周围的土轻轻刨开,直到看见笋的根部后,再用锄头将春笋挖起,要避免伤及成年竹子的根部,笋子挖出后,要将土回填,以此保证竹子的正常生长。
冒尖笋刚刚破出土层,笋体大部分还在土中,笋壳脆嫩,颜色多为淡褐色或黄绿色,表面可能带有一些泥土。因为冒头的笋子接受了更多的光照和空气,生长速度快,纤维相对较细,口感就要丰富一些:浓郁的笋香,清爽滑口,滋味鲜美。多用来清炒、煮汤、做馅,更能够突出笋子本身的鲜甜味道。
下过雨后的竹林空气清新,高大的竹子成了这片乐土的守护者,弯腰垂枝都仿佛在打量审视她们。
这片竹林往东有一大片芦苇荡,一眼仿佛望不到头,像波浪连绵起伏,不少候鸟都会选在那里栖息停留。
于是许国平轻易的在竹林中看到了它们留下的羽毛。
连续挖断三个土中笋后,许国平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一屁股坐到地上,先把挖出的泥拢回去,她把断了一半的笋子拿在手上。
“这处坡有点陡,受力不好把握。”她磨磨牙,左右观察,得出结论。
一抹纯白就这样突然闯入她的眼中。
她觉得疑惑,站起身不免朝那边走了几步,身后远远的还有两人的交谈声。
走到面前捡起来时,她才发现是片洁白柔软的细长羽毛。
擦掉手上的泥土,轻捻在手指间,她把目光往远方看去,是白鹭的羽毛。看样子远处的芦苇荡有一群栖息的候鸟。
传说故事里,白鹭往往会带来幸福和平。
许国平抬头看向天空,太阳还未完全出来,光线穿透云层照在竹林间,薄薄的雾气逐渐消散。
她向来不信这些神话传说,事物的意义是人为赋予的,只不过作为心灵情感的寄托罢了。
但是,带回去她们一定会开心。
这样想,她连笋都顾不上挖,几乎把竹林中的羽毛洗劫一空,等吴叶和张铃悦过来的时候就只看见一堆半截的笋头和抓着一把毛的许国平。
两人脸色各异,眯着眼上下打量她。
她被盯得有些发毛,抿抿唇把手上的羽毛推进张铃悦怀里,提起锄头往土坡背后走去。
吴叶和张铃悦相视一眼,随后发出笑声,震得竹枝上的鸟拍着翅膀飞远了。
她们可没看见许国平通红的耳朵。
捡起地上的笋子蹦跶蹦跶的追了上去,嘴上还在打趣的说“怎么害羞了?”
许国平无奈叹气,“等会摔了,就回去和玉华一起喝药吧。”
两人立马噤声,老老实实的跟在许国平背后。
“你们昨天去看过小鬼头了?”搬着东西回到路边,许国平问。
吴叶跺了跺脚上的泥,“对呀,学校老师说他三天没去上课了,也没法联系上他,就找了我,我们火急火燎过去,才发现房奶奶生病卧床呢。”
张铃悦把许国平头发上的落叶取下,“我们到那会他正在屋顶上修瓦,灰头土脸的。”
房奶奶今年六十多了,一个人拉扯孙子长大,身体差一到换季就容易生病。
“那小子自尊心强,没来找我们,跑去码头当临时工。”张铃悦叹气,“那工钱连药都买不起。”
三人一时间无言。
房峻是她们大一市场调查时意外救下的孩子,倔强要强,面对她们的资助也很有骨气的拒绝,还是当时敖玉华话狠,一句“你的尊严连药渣都换不来”给房峻说哭了,最后抽泣着接受了帮助。
但大多时候他都保持着自力更生的状态,打碎牙也往下吞。
这种性格没有什么不好,敖玉华评价,但是,只有蠢货才在意活法。
“倔强不一定是好事,至少对现在这个环境来说。”许国平正色,“房奶奶怎么样?”
张铃悦:“难说,这个春天都不一定能挨过去。”
她说的话很直接,不需要掩饰的直接。
吴叶坦然,“我们只做能做的。”
房峻在金钱方面敏感得很,她们只能从生活方面给予帮助,例如眼前的竹笋。三月中旬春笋质量很高,他拿去卖也好,自己留着也好,都是他的选择。
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些东西微不足道,尤其是在她们的阶层里,掌握社会资源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几乎无法提供帮助,但是对于底层人来说,它会成为接下来生活的依靠。
抓住可利用的一切资源,利用它压榨它,达到效果最大化,是她们的生存准则。
但当温饱都难于维持时,他唯一能保留的是他的自尊,他需要这份选择权,他把它牢牢抓在手上,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舒桐当时的评价给了我重重一击,他们把所有的错误归咎在穷人身上,说‘穷人穷是因为他们不懂变通、不够努力’,你们不知道那一屋子人都变了脸,云生直接拍桌出门。”
“如果努力变通就能改变,大同社会早出现了。”
“这套‘何不食肉糜’的说法我听了几年了,于是我直接建议他去菜市摆张桌子讲书,让全人民思想解放好了。”
吴叶淡笑说完。
“难怪昨晚他对我说少做些无用功。”张铃悦摘下路边一簇野花,微风稀疏的吹动她的发丝。
“问心无愧就足够。”许国平送上安抚的眼神。
林间重重叠叠,枝叶吹呀吹,不远处升起的炊烟为竹林描上白眉,惊飞的鸟在竹间扑朔。空气带有泥土草地的味道,猛猛吸上一口觉得轻松极了。露珠滴落,小草打湿鞋子,蜗牛隐藏在草叶下缓慢爬行,轰轰的汽车声与一切格格不入。
张铃悦坐在副驾驶,头偏向窗外,手搭在窗口,偶尔撑住脑袋。她不算是锋利型的外貌,尤其一双眼睛灵动清澈,总让人觉得无辜,但她的睫毛生得长,轻轻低垂就足够遮掩,所以她面对外人,会选择收起笑敛住眉,以此隐藏自己的弱点。
当人第一眼见到她,便会忘记她外表带来的柔弱感,转而被她气质所震慑。司机在张家待了两年,见识过她的雷霆手段,此刻只安静的开着车,巴不得连气息都消失。
后座的吴叶抱着许国平的手臂正打盹,两人头靠着头,一晃一晃的,张铃悦顺着后视镜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眉眼弯弯。
车开过芦苇荡,高度不一的芦苇黄绿交织,仿佛一片绿色的绸缎在风中荡漾,白鹭和野鸭在远处嬉戏,像是春天的交响曲,生机热闹。
张铃悦很适时的想起了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动物尚且知道春天的到来,更何况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