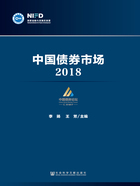
2.1 金融运行的宏观经济背景
全球经济在本轮复苏中经历了2016年的企稳和随后两年的持续改善,但2018年的经济运行呈现逐步逼近短周期顶部的迹象,主要体现在:2018年全球经济持续改善的动能有所衰竭,IMF近期将2018年、2019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值均下调至3.70%,与2017年的增长水平基本持平;全球贸易增速出现显著下滑,从2017年的5.2%下降至2018年的4.2%,预计2019年将继续下探;虽然2018年的原油价格增速再创新高,但非燃油价格增长已显露疲态(见图2-1)。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以来,人口老龄化危机、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下降等严重制约全球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2018年全球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以及金融环境持续收紧等因素,使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图2-1 全球经济运行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IMF数据整理;2018年和2019年数据为IMF预测值。
在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是自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复苏最为稳健的,主要源于其推动经济复苏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有效切换。第一阶段采用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进程的持续推进,奥巴马时期的需求端刺激逐步转向第二阶段的特朗普时期以减税为代表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拉长了经济复苏的周期。如果特朗普的减税和基建等经济政策能同时发力,美国经济在未来两年的复苏进程仍将保持强劲。问题在于,尽管政府赤字的扩张推动了美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但美国如果不尽快放缓债务增长,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势必会受到较大阻碍。同时,贸易摩擦升级引发的美国输入型通胀,叠加减税、基建投资带来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可能倒逼美联储在未来两年持续加息,进而增加发债的财务成本。在此背景下,如果政府债务的增长受限,大规模基建投资便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复苏在边际上很难继续走强。种种迹象表明,依靠量化宽松或债务拉动型的增长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或全面复苏,最终只能依靠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
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端拉动的合力下,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的复苏保持同步,2016年企稳,2017年持续改善。但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有所凸显,前3个季度经济增速逐步下移,并于第三季度录得6.5%,略高于2009年第三季度的最低值6.4%。然而,经济下行压力并没有撼动中央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的决心。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断改善,例如,中国工业过剩产能初步出清,工业企业的赢利能力逐步增强,房地产库存明显去化,宏观杠杆率趋稳。这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引致2018年经济增速趋势性下行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净出口成为中国经济近两年的主要扰动项,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6年的-9.6%,跃升至2017年的9.1%,再跌至2018年第三季度的-9.8%。在中美贸易争端长期化及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趋势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速可能持续收窄,进而会继续对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造成负向的拉动作用。其二,2018年以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在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背景下,“堵偏门”和“开正门”等相关政策没能实现有效衔接。受资产新规和政府财政整顿的影响,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受到极大限制,然而,地方政府举债的“正门”并未及时扩容,地方政府债的发行量没有相应增长,反而在2018年前8个月一直呈现萎缩的趋势。随着第四季度地方政府债发行的提速,基建投资增速有望企稳,进而缓冲由基建投资不稳引发的经济下行压力。其三,实体融资遭遇困境。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中小企业融资通常出现恶化。但2018年以来导致实体部门融资困境的因素还包括:首先,资管业务一直是中小企业成本相对较低的重要融资渠道,在银行“回表”之后,部分中小企业失去了通过表外融资的渠道,但由于缺乏资质又无法以传统信贷或标准债权等方式获得融资。其次,部分实体部门融资需求受到管控,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管控会持续加强,此外,从房地产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和中央“严控房价上涨”的政策导向看,房地产的融资政策在短期也较难改变。实体经济两个主要融资部门的需求受到抑制,导致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降低。
从供给端看,表2-1描述了要素投入和TFP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关系。其一,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次贷危机以来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但资本存量的增速没有跟随潜在增长率下滑,反而小幅上升,这就导致资本效率大幅下滑,即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其二,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投入增长率在危机后也呈现大幅下滑的迹象,进而导致劳动投入对潜在增长的贡献下滑。其三,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的同时,TFP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也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上述数据说明,次贷危机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刺激资本积累的方式实现,但是在人口老龄化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扭转TFP对增长贡献份额较低的现状,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持续下滑。为此,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提高全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提高TFP对增长的贡献水平,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的发展。
表2-1 中国经济生产函数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