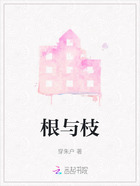
第1章 木箱里的族谱
一、泛黄的户口本
2003年深秋的夜晚,十二岁的我蜷缩在阁楼木箱前。潮湿的霉味混着樟脑丸的气息,指腹擦过户口本“曾祖父”栏时,突然发现母亲的姓氏与“祖母”并排而列。月光穿过天窗照在“入赘”两个蓝黑色钢笔字上,油墨晕染的痕迹像极了奶奶生前常绣的并蒂莲。
阁楼木梯突然吱呀作响,我慌忙将户口本塞回奶奶陪嫁的描金漆盒。转身却撞见爷爷拎着煤油灯立在梯口,昏黄光晕里,他灰白的中山装泛着经年累月的浆洗痕迹。那是他参加村小校庆才舍得穿的衣裳,此刻却皱巴巴裹在佝偻的脊背上。
“在看老物件啊?”爷爷的乡音裹着烟叶的苦香,目光掠过漆盒时,浑浊的眼珠骤然清明如少年。我永远记得那晚他讲述的家族秘辛:1951年冬,十六岁的他背着半册《文心雕龙》逃出祖宅,母亲用红绸裹着族谱塞进他怀里时,城隍庙的钟声正敲响第七下。
二、倒插门的父亲
村口老槐树下,铁蛋他们常围着我学跛脚张瘸子的腔调:“林阿毛,你爹是踩着女人裤腰带进村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何总拿这事取乐。直到有次在晒谷场看见春生叔抱着儿子骑脖颈,暖黄的夕阳里,那个骑在父亲肩头的身影突然让我喉咙发紧。
“要爹作甚?”我故意把弹弓对准铁蛋家瓦檐下的麻雀窝,“没见孙寡妇家五个娃照样活得滋润?”这话惹得众人哄笑,我却盯着麻雀扑棱棱飞向云端。傍晚回家时,看见爷爷在院中给南瓜藤搭竹架,斜阳将他瘦长的影子折成两截,恰似当年他带着襁褎中的父亲跪在邻村祠堂前的模样。
三、残简里的书香
2006年我考上县重点高中那天,爷爷破例取出珍藏的梨花木匣。褪色的红绸里躺着半块刻着“文魁”二字的砚台残片,墨池里凝结的松烟墨竟还透着幽香。“这是光绪年间老太爷中举时用的。”他布满老茧的拇指摩挲着裂痕,“当年家里藏书楼有三进,最里头藏着宋版《梦溪笔谈》...”
四、清明的族魂
每年清明跟着爷爷翻过后山,总能看见他对着野坟茔行三跪九叩大礼。去年春天,他指着西边坡地那片油菜花田:“瞧见那棵歪脖子柏树没?底下埋着咱家迁来的高祖。”花浪起伏间,他如数家珍地讲述光绪三年大旱,高祖如何带着族人翻山越岭来到荒芜的地方,用辛苦、汗水和智慧在异乡垦出三十亩水浇地。
最难忘的是他讲述同治年间那场争水械斗。邻村唐家半夜往水源地倒粪桶,太爷爷带着十二个族中子弟,举着火把在县衙门前跪了三天三夜。后来孙子碧垣大人考中拔贡,县太爷亲自批了引水渠文书,爷爷说到此处时,枯枝般的手指划过新立的青石碑,仿佛触摸到了那些沸腾着热血与智慧的族魂。
五、流动的族脉
大学寒假归家,我带着地方志复印件与爷爷对坐炉前。泛黄的县志记载着光绪二十八年林氏捐建义塾的碑文,与爷爷口述的“五进藏书楼”仅隔着半页泛潮的纸张。炉火噼啪作响,他眯眼辨认着铅字:“当年那些老物件虽不在了,可你看看...”枯瘦的指尖点向窗外,月光正流淌爷爷的脸上,若有所思。
由于骨子里对这些古老物品的喜欢,我也经常联系如今在省图书馆工作的一位高中同学,他会经常带我看看古籍修复室里的残卷。那些虫蛀的纸页在他的手重获新生时,总会想起爷爷临终前攥着我的手,将族谱复印件和半块端砚放进我掌心。春日的穿堂风掠过老宅天井,带着陈年墨香与新竹的清气,恍惚间似有百代文脉在血脉中奔涌不息。只是可惜我没有完成他的愿望,没能成为一个在他看来很是敬重的文人,他虽然目不识丁,但是说起那些往事,眼神里都变得很有光芒。我不由在想,若有平行时空,他又该是如何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