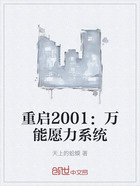
第42章 山里(1)
山上的人越来越多。
除了最早那批人,后来又陆续添了人手:
两个个保姆,一个园丁,一个维修工,一个厨师,还有一个从青城山下请上来的保健医生,专门照看两位老人。虽然王磊已经把他们的旧伤调理的差不多了,但还是需要人照顾。
厨房要多备粮,客房要多打扫,就连菜板、毛巾、消毒水都得换着轮班用。
原本轻松的生活节奏,逐渐变得细密起来。
苏京台那天没多说什么,只在茶后慢悠悠丢下一句:
“既然人多了,山就不能只是‘住’的地方。”
“想办法,让这地方能自己活着。”
徐丽萍愣了一下。
“你是说……自给自足?”
“山上种菜、养殖、留人、养人、教人,全都可以。”苏老说着,抬手指向窗外,“这么大的地段,不动,就永远是花钱;要动起来。”
他没给具体方法,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你可以去村里请几个人来种地,先试试看。”
那一刻,徐丽萍心中突然明白——
苏老看似讲“管理”,其实是在教她怎么构建一个可掌控的现实小世界。
她开始往山下走。
去村里转,挨家挨户打招呼,帮村民孩子送点文具,买点他们自己种的青菜水果。
再挑几个可靠的——请他们轮流上山做短工,一天两顿饭,工资按周结。
李倩最开始只在旁边看着,直到沈芝月冷冷一句:
“配合她,不是帮她,是你在锻炼跨职能协调。”
她才意识到——这不只是“徐丽萍的事”。
于是她着手建立“山上外援协作流程”,跟本地村委打通对接,制定访客登记、合同签约、突发事件处理等制度,并每周亲自参与一次与村民的茶叙会。
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人——
一个内敛稳重,走得慢但扎得深;
一个果断强势,冲得快但有棱角。
可就是这两个,开始慢慢形成一种稳定的节奏。
李倩负责立架子、定规范、提节奏;
徐丽萍负责把人带住、安好、稳心。
她们谁也没说要争高下,反而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苏老有次在晨练后感慨:“你看这两人,终于像个‘左手管人、右手管事’的样子了。”
沈芝月却只是哼了一声:“不过刚起步,还远。”
但眼神里,已没有了当初的审视。
转眼几个月过去。
山上的地被开出两片:一块种菜,一块建了个猪圈和鸡舍,粪便集中处理,生活垃圾开始分类,甚至雨水都引流入蓄池。
山里人越来越多,却越来越有序。
就连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也开始说起:“王家山上的那些人,不像外地老板,是好人。”
王磊没管这一切,他只在某天下午,看着两个女人站在山道口,对着刚送来的一批建筑材料交接签字、安排卸货、顺便聊起各自明天的时间安排。
他笑着把一盏安吉白茶递给苏老,随口道:
“她们两个现在还可以?”
苏老没回答,只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轻轻放下。
“先让她们再滚几次泥巴。”
“干净人,走不远。”
日子静静流动。
没有仪式,也没有课表。
苏京台的教学,从不设“课”。
他只在每天清晨饭后,独坐书房泡茶,徐丽萍若愿意听,就坐在对面。
一开始,她拘谨,像个学生。
但苏老却从不讲道理,只随口问:“昨天的物资对账,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厨房排班为啥最近出入人手频繁?”
“你觉得,山上的人,谁是‘心头有活儿’的,谁是‘混日子的’?”
每一个问题,看起来像闲聊,其实都在拨她的神经线,让她学会观察,看人,看局,看细节中潜藏的力量。
有时候,苏老一整天不说话,只在傍晚随口一句:
“管理从来不是压,是让他们自己知道你盯着。”
徐丽萍没回话,只回屋做了张“影子值班表”,默默观察整整一周,没动声色地换掉了一个“嘴勤手懒”的保姆。
再后来,苏京台会开始讲些旧事——某省调研某地时,如何识人;某年官场震荡时,哪些是“表忠”,哪些是“真干”。
那些话,她听着像故事,记下时却突然发现:她的格局,变了。
———
另一边。
沈芝月则截然不同。
她每天只讲一个小时,不多也不少。
没有废话,直接开干。
第一天,她让李倩列一张“山上所有角色的工作清单”,包含职责、工作边界、替代性和协同性。
李倩熬了两晚,列了三大页。
沈芝月只看了一眼:“太多,没重点,扔掉重写。”
第二天,她要李倩拆解一个“招待流程”,精细到“来客喝的是热水还是温水、玻璃杯还是陶瓷杯”的标准流程和背后逻辑。
李倩几次被呛得脸红脖子粗,有一晚上甚至回房差点哭出来。
但到了第五天,她咬牙做了份招待SOP,被沈芝月扫完后,破天荒地点头道:“合格。”
“你不是不会。”沈芝月淡淡道,“你只是以前没人逼你。”
从那天起,李倩的眼神就变了。
她学会了不吭声的时候听得更仔细,发言前先在脑子里过两遍。
她原本是个聪明人,现在正被打磨成一个“聪明而不逞强”的人。
王磊始终没插手,只偶尔在午后看她们拿着笔记本走过长廊。
贺青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脚步慢下来,声音也低下来。
可她的眼睛却比以前更亮了,尤其是每次看到王磊为人施针的时候。
王磊没主动教她。
他从来不是个主动去“培养别人”的人。
但他治病从不避她,只要她在,他也不赶。
有时苏老、沈老饭后让王磊顺手开一方,贺青桐就在旁边静静看着,站得不近不远。
可治完病后,他却常常转头看她一眼,随口一句:
“那条脉是不是滑?你刚才有没有感觉气一下子泄了?”
“你觉得我用的是‘三阳调’,还是‘转骨法’?”
起初她只能模模糊糊地答,有时甚至根本没看出来。
王磊也不急,只是轻轻笑笑:
“没事,哪有人第一眼就能看到‘气沉丹田’的。”
“多看几次,别眨眼。”
贺青桐便更加认真地盯着。
她不像从前那样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学会”,她开始学着去“理解”。
理解脉下的沉浮、针入的角度、气机在指尖的轻颤。
有一次,王磊在给沈芝月调理腰伤,针落得极深极稳。
她忽然皱了皱眉,小声道:“你是不是用了‘反钩针’?”
王磊挑了挑眉,笑了:“你怎么知道?”
“感觉……她气浮得慢了一点,但你最后那一转,是钩住的。”
王磊抿了一口茶,没有回答,只淡淡一句:
“可以啊,开始开窍了。”
从那以后,王磊每次行医,她几乎都在。
那一天,王磊看着她为厨房的一个保姆贴艾条、揉肩、敷药。
手法虽然还生涩,但节奏很稳。
他站在门口没说话,只笑了一下,轻轻叹了口气:
“这女人啊……天生就是干医生的命。”
2002年冬,山上落了第一场雪。
竹叶压着白霜,院墙上结了薄冰,空气冷冽得像刚削开的梨。
贺青桐提前半个月发动。
产房早已准备好,馨和妇幼医院的产科主任和医护团队也早就驻在山上,所有人都知道那一天迟早要来。
但真正到来时,依旧让人心跳加快。
徐丽萍在产房外来回踱步,李倩守着热水和保暖衣物,连平时最淡定的沈芝月也不动声色地坐在廊下,耳朵却一直朝那间屋子。
王磊没进去。
他坐在客厅一角,手里握着茶杯,茶已经凉了半盏,却一口没动。
直到一声婴儿的啼哭穿破冬日的山雾。
王磊这才放下茶杯,轻轻吐出一口气。
门开了,产科主任笑着点头:“母子平安,男孩,七斤三两。”
众人一瞬间松了口气。
徐丽萍悄悄抹了把眼角。
李倩小声笑:“这回,‘王家军’真成编制了。”
王磊走到产房门口,看着刚刚被安置好的贺青桐。
她脸色有些苍白,眼神却清醒,一看到他,轻轻张了下嘴唇:“二胎政策放开了吗?”
王磊笑了:“没放,但我们家先搞试点。”
她眨了下眼,声音哑哑的:“名字想好了吗?”
王磊一只手握住她的,另一只手轻轻抚了抚襁褓里孩子的脸蛋。
“王周二。”
贺青桐愣了一下,然后嘴角一点点扬起,像一朵刚冒出雪地的梅花。
“你这人……也太敷衍了。”
王磊无辜摊手:“你们仨都说孩子归我起名的,那我可就真起了。”
沈芝月远远坐在廊下,听见这个名字,终于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苏京台却笑出了声,叹了句:“有王磊这性子,孩子起名不出奇,才奇怪。”
屋外风雪渐停。
屋里多了一个新生命,一家人,又多了一份热腾腾的牵挂。
而王磊低头看着那个新生的孩子,眼里闪过一抹柔光——
“来吧,小子。等你哥上幼儿园,我们就下山。”
贺青桐生了孩子,屋子里多了一口奶香,热热闹闹的。
徐丽萍也恢复了点睡眠时间,开始慢慢能抽空做些自己的事。
整个别墅的节奏,终于从“团体备战状态”,慢慢过渡到了“稳定运行”。
唯一有些……“被冷落”的,只有王磊。
他这段时间真是过得清苦。
贺青桐不能动,徐丽萍天天带着王周一轮番学习、带娃两头跑,晚上常常抱着育儿笔记睡着。
至于李倩,别看白天嘴贫得很,晚上房门一关,比谁都严肃。
王磊敲门三次,三次都是一句:“别闹,我在整理沈老师的案例。”
——被推了出去,像个偷鸡不成的流浪汉。
这天深夜,王磊实在闲得慌,抱着一杯牛奶坐在书房打坐,突然听见李倩房门开了。
她披着件毛绒外套,眼神有点倦,头发都乱了。
王磊立刻跟上,笑吟吟地走过去:“哟,舍得出来了?”
李倩白了他一眼:“没水了,我下来倒点。”
王磊跟着她进厨房,看着她倒水,又瞄了一眼她锁得死死的房门。
“你说你啊,天天搞学习,熬夜又掉头发,也不怕提前变成女苏老?”
李倩喝了一口热水,轻轻叹了口气:“不努力点,你敢把山下交给我吗?”
王磊靠在门框上,慢吞吞地说:“可问题是,我现在交不了你事啊,你总得给我留点……人生乐趣。”
李倩噗嗤一声笑出来,摇头:“你少来。”
王磊上前一步,轻轻捏了捏她的手指:“青桐不能动,丽萍要带娃,现在全山头就你还有活动能力了。”
“你这样天天画表格写方案,我这荒凉的身心哪受得住?”
李倩抽回手,假装认真道:“你这是在给我减压,还是在给你自己争取福利?”
王磊笑得很无赖:“双赢嘛,毕竟青桐孩子都出生了,你也得抓紧。”
李倩低头,耳根微红。
半晌,她轻声嘀咕了一句:“我这不是自作孽嘛……”
王磊眼睛一亮:“你自己说的啊,那我就帮你解脱——现在学习暂停两天,任务变更,由我亲自安排。”
李倩嘴上还在抵抗:“我还要做交叉访谈报告……”
可下一秒,她已经被王磊拉着往楼上走。
她没再推开他。也没再提计划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