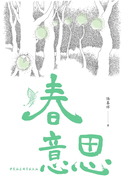
幸运的汪国真
汪国真是谁?一位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令许多少男少女为之动情的诗人。有媒体日前报道,汪国真沉寂了十几年后于去年复出,但出版的《汪国真诗文集》无人问津,近来以写招牌维持生活。
20世纪80年代我在做语文教师的时候,诗坛刮起两股强劲之风,一个是汪国真,一个是席慕蓉,记得我曾托人带过好几盘席诗磁带,既有课堂上用的,也有替学生买的。我的印象中,汪国真的诗属于浅白的那种,不像大部分诗人那样哲学艰深的。那时念诗和作诗都是很时髦的,显得很有文化的样子。可时过境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环境大大不同于现在,社会生活表面的多样性,实现个人价值表面上的多种可能性,使大众的心态远离了诗歌的语言节奏,于是诗歌变成像考古一样的东西;另外,从出版角度观察,诗歌在近十年成了最不受出版商欢迎的文体,没有人把关注中国诗歌的发展当作义务。
那么,现如今诗人靠诗还有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呢?不说奢侈地生活,清贫总可以吧。比如像国外一样,靠诗朗诵来赚外快,美国、德国的诗人朗诵一次起码要本国货币300元以上。然而我们这儿不行,起码现在不行。按现在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红火劲,总有一些优秀诗作可能撞上大运吧,然而可能性又是极小,除了一些经典作品被分割运用外,你说有哪一部诗作如此走运?那些各式各样的商人想尽办法都无法制造畅销、无法跟市场衔接的时候,诗歌算是彻底遭遇“寒流”了,尽管是暂时的,但我相信这个阶段仍持续一段时间。
然而也有特例。我曾看过一篇报道,说北方有一位“诗人”,最多只算三流,为生活所迫,就在大街上替人即兴“写诗”,诸如将人名嵌入诗,或按卖者框定要求作诗,每首诗最少卖十元,最多可卖到三百元,生意相当不错,据说已赚了好几万元。
因此,汪国真写招牌不是先例,不是说有诗人已经在写招牌了,只是说有许多的诗人老早就开店、做房地产、办公司或改行写影视剧去了。席慕蓉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记忆,汪国真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汪诗人没有在高潮中谢幕,反而像乔丹那样再次复出,这就注定其前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自然也包括乔丹那一类人。
对于汪诗人来说,写招牌并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因为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对某些喜欢炒作的媒体来说,汪国真靠写招牌为生,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这就是真实的社会。
(原载《杭州日报》200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