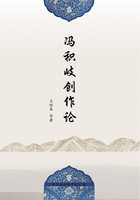
第3章 绪论
陕西作家的本土意识极为强烈,他们的创作就像陕西这个省一样,区域不同,反映在作品中的历史文化、地理风貌、人文情怀亦不同。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绝大部分小说关注故乡约克纳帕塔法,于是文学中就有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种地域与文学的密切关系,陕西作家均有深刻领会。陕西有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区域,每一个区域都被作家们写入了文学作品,他们各自为营,于自己记忆中的“故乡”打捞历史片段,因此即便是同一区域,也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例如,柳青、陈忠实、冯积岐均写关中农村:柳青写的是农业合作化背景下的长安农村;陈忠实写的是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初期的西安东郊农村白鹿原;冯积岐写的是自“文化大革命”至“城镇化”时期的关中西府农村。
与许多陕籍作家相比,冯积岐的创作出发得稍晚,1983年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续绳》,其间,有些陕籍作家已拿到了全国小说奖,但他的创作力极其旺盛,至今为止,已出版了十余部长篇小说,发表了近300篇中短篇小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的创作量年年攀升,尤其是近几年,几乎是一年奉献一部长篇小说,以致不能不说,在目前的陕西文坛,冯积岐是风头正盛的一位。从冯积岐初入文坛算起,至今恰好37年,也就是说,冯积岐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37年献给了文学。他用30多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行一行地填满稿纸的空白,也填满他人生的一个个空白。在这30多年里,冯积岐所获国家级奖项并不多,但他依然“生命不止,创作不息”。因为在短篇小说方面颇有建树,冯积岐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当人们期待他在短篇小说上再创辉煌时,他却将更多的精力投放于长篇小说创作之上。他希望自己的创作“一直在变”,这种变化其实是对于过去的超越,并且他自己也在这种“超越”中欢欣自得,这一切都会让人一再想起陈忠实常说的一句话——“文学是魔鬼”。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创作还远未结束的作家,我们只能尝试着总结冯积岐30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如果要给他的创作赋予几组关键词的话,那就是苦难与权力、欲望与人性、反抗与逃离。苦难的产生源于权力者滥用权力;人类深深地纠缠于欲望之中亦可见人性之丑;存有良知的孤独个体在对抗中一次次遭受挫败而最终选择逃离。从反抗到逃离,用逃离的方式再反抗,由此,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坚持与无奈,忧伤而不绝望,看到了他直面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这又是一个“生错时代的旧理想主义者”,只不过与张承志相比,冯积岐的无奈与无助感似乎要强烈得多。
面对冯积岐如此不绝的创作激情与创作生命力,也许首先应该探讨的是,究竟冯积岐的创作宝库源于何处,或者说究竟是何种力量在支撑着他的创作。他自己曾多次提到三个创作资源,即苦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忧郁的青年生活;关中西府的故土文化,即周文化。前两个是生活资源;后一个是文化资源。
谈到一个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自然容易追溯他的童年经验。童庆炳先生曾指出艺术家的体验包含缺失性体验与丰富性体验。缺失性体验指主体随精神或物质上需要的缺失而引起的痛苦、焦虑等体验。这种缺失激发了作家力图获得对象的顽强意志,也成为很多作家创作的动因。冯积岐的童年体验就是一种缺失性体验,与怯弱相联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儿时有一次啃萝卜时发现有人在后面追,慌乱奔跑中掉进了水井。多年之后他回忆起来,自己之所以奔跑,并非是后面有人追赶,而是被水井周遭的茅草迷惑,以为这堆茅草能将自己掩藏起来。因为年幼,童年时期冯积岐对于饥饿的记忆并不深刻,在这篇文章中,生理需要即衣食住行的缺失尚不明显,所缺的是安全感与爱。对周遭的世界缺乏安全感,他希望茅草将自己掩藏起来;被三叔抱上来之后,他心头“渗进了一股暖意,有了做人的安宁感”[1],满足了作为一个人被他人关爱的需要。这两种需要的缺失导致幼时的他对于这个世界产生了怯意与慌乱,以及渴望逃离的孤独感。
“文化大革命”开始,冯积岐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他成了“地主娃”。政治身份被剥夺,读书权利也被剥夺,饥饿、劳累开始成为他的老朋友,还有陪斗、被训话、目睹家产被抄……在生理、心理上均遭受摧残。政治身份被歧视,就意味着一切都被否定。原本还能点着煤油灯囫囵吞枣地读小说,以“读书”作为生活的唯一乐趣,甚至证明自己为“人”的唯一证据,但这种乐趣与证据因为政治运动失去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以及尊严的需要均缺失,更无法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童年、少年时期,冯积岐的需要缺失越严重,欲望也就越强烈,当老师让他用“人”造句时,小小的他竟造出了“我是人”“我娘是人”的句子。冯积岐的童年、少年时期,用“苦难”二字概括毫不为过。
青年时期是幼年到成年的过渡阶段,是人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最有发展优势的年龄阶段,也是一个人开始自觉实现自我价值的时期。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冯积岐由少年时期步入青年时代的路途走得极为艰难,他的青年时代被卑下的阶级身份压得苍白,合法身份尚且要受到质疑,更何况成家立业。20岁时,他的“成家”问题算是解决得比较偶然却也顺意;“立业”则到了30岁,因为他的文学能力。1983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因写作才能受到乡领导的重视,他被推荐到岐山县北郭乡广播站当通讯员,虽然不是“正式工”,但与一般农民相比,他还是半脱产的干部。1990年冯积岐由西北大学作家班毕业,在《延河》杂志编辑部帮忙。1994年,41岁的冯积岐转正,成为作协机关干部。这能否看作经历多年苦难与折磨的冯积岐终于修成正果?
缺失性的生活体验使冯积岐的创作一出发就带上了苦难、困惑、质疑与出逃的渴望,这种创作风格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冯积岐的故乡岐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是青铜器之乡。岐周文化以“尊德”为主导,在这一文化孕育下的民众性格纯朴、传统、好礼仪,同时又有着目光短浅、保守、好面子等负面的因素。周文化作为冯积岐创作的资源,其主要意义不在于他的作品中呈现了一系列的西周文化要素,而是人物文化性格的塑造。他的小说背景多是“松陵村”,这个松陵村就是被周文化浸染的村子,村子民众淳朴、谦和,有的甚至还有“利他主义”的性格因子,如《沉默的季节》中的周雨言、《村子》中的祝永达、《粉碎》中的景解放,塑造这三个人物的时间前后相差了12年,但彼此却有相似性:他们有一番抱负,遭遇了两次婚变,渴望为农村的发展贡献自我,可见他们身上所带有的“礼仪”文化。第一次婚变预示着传统文化遭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第二次婚变预示着他们依然在固守传统。但就整个陕西关中地区的文化性格而言,都有着淳朴、传统与保守的一面,加上冯积岐并未有意彰显整个岐周文化的个性,因此这一文化资源在冯积岐的创作中并不明显。
实际上,除了这三个资源。笔者认为还应该提到的文学资源,是冯积岐不断阅读的经典作品。如果说生活资源与文化资源给了他创作的根基,那文学资源就给了他飞翔的翅膀。冯积岐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他对经典,尤其是欧美文学的阅读给他“打开了天窗”[2],他读契诃夫、莫泊桑,了解了短篇小说结尾的重要性;读梅里美、欧·亨利、乔伊斯,懂得了每篇小说应各有各的滋味……不断地阅读,让他逐渐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学品位。阅读也强化了他的写作技巧,他的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有自己的风格就得益于此;阅读又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即“文学是心灵史”,因此他的长篇小说并不重在展示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而是追溯人的心灵史,具体来说,就是揭示人性中最隐秘的地方,也即人性的弱点。
纵观冯积岐30余年的小说,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苦难。冯积岐的作品中总有一种无法排遣的忧愁,这种忧愁与苦难相连,有时甚至是由一系列苦难组成,这些苦难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无奈地叹息;读得多了,即便有快乐的场面,也总让人提心吊胆,因为短暂的快乐之后往往是更深的苦难。这种苦难有农民因衣食住行而来的生的艰难,也有文化人渴望自我而不得的活的艰难。苦难不是源于农民的愚昧、懦弱,而是出于权力者的压迫,因此文化人面对苦难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启蒙者,而是与苦难的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苦难的承受者。不过农民所承受的更多是肉体之痛,而文化人却是精神之痛。面对他作品中的苦难,有时也不免要问,冯积岐究竟为何要如此固执地撕开生活中那些美丽的薄纱,露出惨不忍睹的滴血伤疤?在消费时代,各种娱乐方式铺天盖地,时下的读者已经习惯了在哈哈一笑中酣然入睡,有谁愿意被压抑得喘不过气的世界纠缠住原本就已脆弱、经不起半点风吹草动的神经?不如就迎合大众,互相消费,人生不过一场戏。可是,不,冯积岐说我们太习惯了遗忘,看见了镀金的天空,就忘记了死者的倒影。鲁迅当年也曾指出民众的健忘,但是今天的冯积岐已没有当年鲁迅的启蒙者姿态。鲁迅尚且渴望做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在众声喧哗的今天,人人都在毫无秩序地振臂呼喊,呼喊的声音似乎也在为这个世界添乱,那索性挖掘苦难,亮出伤疤,为了“让大家看个明白以便于治疗”[3],这也足见冯积岐面对苦难的勇气与无奈。
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批判。冯积岐小说的批判力度力透纸背,这种批判多伴随着苦难叙述展开,批判所指为权力、专制。在思想专制的年代,拥有政治权力就拥有了对他人的生杀予夺之权,人性、人道主义被彻底抛弃;在“改革”年代,一些基层领导者同样滥用权职,肆无忌惮地践踏他人的生命,底层民众却无从反抗。在权力的极度压制下,底层农民只有卑微地生活着。批判力度在他的短篇小说可能表现得更突出,有的一开篇不着痕迹,故事在絮絮叨叨中展开,带点魔幻色彩,加上突兀的情节,看到似懂非懂之处,突然在悲剧氛围中结束,让人莫名其妙,思考再三,感觉在批判什么,但那究竟是什么,却又说不透,因为说不透,批判的意味反而更浓。比如《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故乡来了一位陌生人》《目睹过的或未了却的事情》《革命年代里的排练和演出》,批判的是特殊的年代、集权的体制,也是大众的麻木。关于小说的批判力度,冯积岐是有意并极力为之的。与书写苦难一样,批判的目的同样是在揭示真相,他曾说:“在一个被扭曲的时代,尤其是当浊流滚滚而来时候,有良知的作家要明白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的分量有多重”,要“坚守人民立场,坚守艺术立场,坚守批判立场,这是一个好的作家最起码要遵循的原则”“一个清醒的作家必须和时代保持距离,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这是最低的起点”[4]。冯积岐的创作坚守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这一立场增添了他小说的思想深度。
读来最耐人寻味的是技巧。以创作先锋小说起步的冯积岐把小说当作一种艺术,“怎么写”自然是他极为在意的事,他的小说多从故事结构、叙述角度、叙述语言等方面来彰显个性。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小说有“小说味”,有“味”的小说则应该在写作技巧与写作内容上高度契合,且使小说具有鲜明的个性。“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和谐整一使冯积岐的小说味纯正耐嚼”[5],因为他把写作视为生活,因此下笔才小心翼翼。即便是一个短篇,有了题材他也不会轻易下笔,而是要先找一个合适的叙事角度。乡间祈子有“撵香头”的习俗,《去年今日》写的就是与这一习俗相关的简单故事,一个叫列列的女子因“撵香头”得了儿子,第二年去还愿时,她却突然想找到去年与她夜宿窑洞的陌生男人,等她终于看到时,那人正跟着另一个女人进了窑洞。冯积岐将这篇小说写得极为耐读,开头部分写得像一首优美的诗,结尾则像一首哀怨的歌。今年与去年穿插进行,故事背景并不说透,一开篇列列内心的渴求还不明朗,等她要求再逛一次庙会时,便逐渐清晰,到最后她失望地流泪走开时,她隐秘的内心世界才被完全揭开。除了叙事角度之多样,阅读冯积岐的小说,还容易被他的语言所吸引,冯积岐所用的是一种极富有诗意、感性与理性杂糅,并融合多种修辞手法的文学语言,像一条河流,平静处诗意灵性,激烈处犀利悲愤,艺术感染力不言自明。
冯积岐是一位自我意识较强的倾诉型作家,他大部分作品都绕不开个人经历。他的人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地主娃”、农民、作家,他的作品也选取“地主娃”与文化人的视角,主要关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主娃”,“改革”时期的农民以及文化人,写他们的爱恨苦累。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在揭示苦难、批判权力、彰显人性之丑。2011年以《逃离》为标志,他的小说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向对人性的关注,语言较之前期平实许多,开始发掘人性之善;而在《粉碎》中,人性之善被张扬到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一方面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可喜的信号,那就是冯积岐已挣脱束缚他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情结,也许多年之后,他再次书写“文化大革命”故事,会抛弃他以往“文化大革命”书写中的“个人情绪”,更多地站在民族发展的立场上,客观、全面地审视这一段历史;另一方面又不免令人担忧,他的“批判立场”是用多年的创作积累起来的带有个性特色的写作姿态,一旦放弃这一姿态,他将以何种方式彰显自我?此外,从人性之恶到人性向善,都不过是选择了人性的两极,也许更需要揭示的还是人性中既恶又善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注释
[1]冯积岐:《将人说诉说给自己听》,《萌芽》1992年第6期。
[2]冯积岐:《读书》,《延河》2010年第7期。
[3]冯积岐:《自序》,载《小说三十篇》,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5]夏子:《午后之死——冯积岐和他的小说》,《小说评论》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