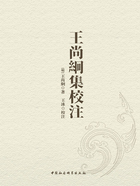
前言
王尚絅(一四七八—一五三一),字錦夫,號蒼谷,明代河南郟縣人,著名文學家、理學家。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著有《平山年譜》《義方堂集》《維正稿》《嵩游集》《密止堂稿》《西行類稿》等,著作大部分亡佚。国内現存文集有明刻本《蒼谷集錄》残卷六卷、清刻本《蒼谷全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成化戊戌十年(一四七八)二月,王尚絅出生在一個具有深厚儒學傳統的家庭裏。父親王璇,字平山,『為人恭厚淵懿,言章而理,道穹而遜』[一],『警哲有氣概。……考定《冠射古禮》及《大學中庸心法》,著《謙卦圖贊》,學者稱平山先生。』[二]在父親的教育和影響下,王尚絅『性穎悟,童日即有志于聖賢之學』[三]。弘治八年(一四九五)舉河南鄉貢,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中進士,任兵部職方主事。弘治十六年(一五〇三),父親去世,回鄉守喪。正德元年(一五〇六),武宗朱厚照登上帝位,王尚絅免喪除舊職。正德三年(一五〇八)調吏部稽勳司,次年調驗封司員外郎,任稽勳司郎中。此時正德皇帝重用劉瑾、谷大用、魏彬等人,華蓋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大夏、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戶部尚書韓文等先後遭到殺害或黜退,朝政污濁荒誕,王尚絅於正德七年(一五一二)申請外調,調山西任左參政。同年以祖母和母親垂老,引疾抗疏,未等皇帝允准即攜家南歸。自此隱居郟縣蒼谷山和密止堂等處,前後凡一十三年。嘉靖四年(一五二五),調任陝西參政,時陝西邊防有警,三邊總制楊一清將入閣為相,即付以兵權,不一月敵平。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再調山西任右參政使。嘉靖九年(一五三〇)調任浙江右布政使,任職期間,夙夜勤勩,第二年(一五三一)卒於官。
一
王尚絅是明代文學復古運動中的一位重要文學家,在文學復古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何景明曾將其與王九思、康海、李夢陽、邊貢、何瑭一起稱為『六子』。何景明在《六子詩序》中說:『六子者,皆當時名士也。余以不類得承契納,輔志勵益者多矣。』其《六子詩·王職方尚絅》稱:『職方吾益友,契誼鮮與同。少齡負奇才,萬里飄雲鴻。手中握靈芝,高操厲孤桐。讀書邁左思,識字過揚雄。為辭多所述,結藻揚華風。寸心索相許,撫志慚微躬。』[四]在《寄王職方》詩中說:『故人王郎天上客,一歲寄書凡兩束。』[五]對王尚絅的文學創作才華給予了高度贊許。現代著名學者、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先生在《茶陵派與復古派》一文中指出:『從弘治十五年到正德六年是復古運動蓬勃高漲的階段。……在文學上,復古派終於與茶陵派脫鉤,走向獨立與成熟。弘治十五年和十八年的新進士中,又有不少人加入到復古派陣營中來,其中知名者有康海、何景明、王廷相、王尚絅、何瑭(以上俱為十五年進士)、徐禎卿、王韋、鄭善夫、孟洋、崔銑、殷雲霄(以上俱為十八年進士)。他們的加入,使復古派增添了新的生力軍,陣容更加壯大。』[六]後來廖先生又在其專著《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中,將王尚絅列為以何景明為核心的『信陽作家群』,並將这一作家群的創作風格概括為『沉穩深秀』。[七]黃卓越先生在《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一書中,將王尚絅視為前七子派主要成員之一。[八]
作為著名文學家,王尚絅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創作了大量具有深廣現實內容的優秀作品,表達他對民生和社会治的關切,記錄他與當時文學家的交往,再現自己的讀書與生活狀况,提出自己的文學見解和主張,為明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王尚絅的大量詩文,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民的苦難生存境遇。其中有的描寫了自然災害和社會負擔給人民造成的無窮痛苦,如:『夏來田禾旱,秋來田禾水。大旱禾無根,大水禾生耳。冬寒苦夜長,日長怨春晷。長夜尚可支,日長忍餓死。餓死忍有期,租稅從誰起?哀哀歎田禾,往訴明天子。天子省田家,溝中亂如麻。』(卷二《田禾歎》)老百姓遭受水旱災害,忍凍受餓,溝壑中到處是餓死的人們。《藍靛根》(卷二)一詩寫道:『莨莠不成米,蒺藜未可飱。何知藍靛草,結根傍水村。顧維通稔歲,秖以厭雞豚。乃今華屋子,競取供朝昏。』熟稔年份喂雞喂猪的藍靛根等,如今連富貴家庭也都競相食用。但是,即便如此,人們並不怕餓死,卻仍怕租稅無從交納。人民群眾在自然災害和繁重賦稅的雙重擠壓之下,生活悲慘,走投無路,『乾坤滿目無安土,何處天衢尚可逃。』(卷四《苦雨》)觸目所見,到處都是『繿縷無完衣,傴僂私相語。雖然今日活,不知明日死。不知後日死,不知今日死』(卷一《步出上東門》)的淒慘景象。有的則真實地反映了戰爭造成的蕭條景象,如:『中原昔喪亂,義姑出里門。遂使千載下,抱哥猶名村。伏臘走祠廟,義姑儼有神。維兹困饑饉,迯亡盡四隣。空過抱哥村,不見抱哥人。』(卷二《過抱哥村》)又如『百感經心旅病餘,晚憑長几獨躊躇。飛龍日角慚通籍,別鴈山南候遠書。異域豺狐按壘捷,中原雞犬半成墟。逢人欲問安劉事,何處南陽有故廬。』(卷四《病中六首》之二)中原地區由於戰亂,半成廢墟,人民生活極度痛苦。
面對這種悲慘的社會現實,王尚絅愛國憂民,希望出現更多的賢良之士為民解困。《送惲僉憲兵備湖南》(卷四)一诗写道:『湖水湖山勢欲吞,雙旌五月下荆門。風煙出峽乾坤迥,瘴霧浸江日月昏。襄野豺狐千里道,衡陽鴻鴈幾家村。使君能藉廓清力,詞賦騷談未足論。』熱切盼望安邦濟世的諸葛孔明再世,希望自己的好友能不負使命,完成重任,平定戰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对那些刚直不阿、忠诚為民的人物进行熱情歌颂和讚揚。如《讀黃中郎鞏奏》(卷三)一詩對剛直不阿的黃鞏擊節歎賞:『一疏千秋少,沉吟淚自傾。逆鱗心本赤,縛虎氣還平。國勢逢諸葛,人才誤賈生。異時同史傳,空復古來情。』黃鞏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十四年皇帝南巡,黃鞏上疏言『崇正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六事,以死相諫,後被挺杖五十,斥為民,但仍不改立身行道之氣節,被時人稱為直節之士。[九]
嘉靖七年(一五二八),河南災荒嚴重,王尚絅上書皇帝,直言河南『饑民艱苦萬狀,觸目惻心……死不如牛馬,生不如猪狗,種種艱苦……况今所在搶掠,勢艱輙禁,衆口枵腹,指麥為期。然麥秋之期,遥踰百日,不知其何以為計也。』(卷七《獻民艱苦疏》)他提出十六條救荒措施,包括『憫饑饉,卹暴露,捄中戶,暫停徵,懲不信,權糴買,謹預備,廣恩澤,省刑獄,止匠價,崇節義,正服舍,存恤流民,重正官,計處糧站,禁革吏胥里書』等,以期改善民生。
王尚絅热爱家乡,热爱生活,居家侍養二母期間,其足跡遊遍了河南郟縣、汝州、魯山、寶豐、登封、開封、洛陽、鞏義、焦作、濮陽、滎陽、新鄭、靈寶、禹州等地,留下了大量的詩文創作,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中原文化的寶貴文獻。
郟縣是王尚絅的故鄉,他不遺餘力地傳承、弘揚郟縣的歷史文化。在《建題名塔記》(卷七)一文中,王尚絅充滿感情地說道:『郟自春秋來,文武風節,政事勳烈,鏗鍧炳煥,後先輝映。粵漢以下,或以德行、以道藝、以賢良、以孝廉、以茂才、明經諸科,法各為殊,舉於嵩麓汝崖之間者,彬彬如也,代有名臣,義不絕書。』對家鄉悠久豐厚的人文歷史傳統進行了高度的贊揚。
王尚絅還對長眠於郟縣的北宋著名文學家『三蘇』父子表示了由衷的欽敬。如《祭三蘇先生文》(卷十二)文中說:『嗟予髫齔,獲誦蘇文。煥兮風水,郁兮春雲。乃橋用梓,乃桂乃椿。壯兹氣節,欽耳風神。』《祭東坡潁濱文》寫道:『一門萃美,百世揚芳。鐘靈錦里,托體嵩陽。名兮蓋世,神兮此方。』
中嶽嵩山,山勢雄偉,層巒疊嶂,風光秀麗,人文薈萃,歷來是文人墨客嚮往遊覽之勝地。王尚絅也曾多次遊歷嵩山、少林寺風光,並有《嵩游集》詩集。雖然今已不能見其全貌,但我們通過明本中的《嵩游記》一文,還能窺見詩集大貌。正德乙亥(一五一五)年秋,王尚絅攜兒子王同一起游嵩山和少林寺一帶,進行了長達九天的漫游。一路訪古探幽,題詩作賦,睹物懷友。《嵩游記》說:『明正德乙亥,予西歸凡四載已。乃八月十日甲子雨霽,明日出郭西扈澗,攜兒同憩密止堂,又明日丙寅宿蒼谷行窩。同曰:「風高氣清,採藥嵩少,此其時乎?」丁卯,出山后介兩熊山,宿毛家嶺菴,有洞曰前汝、後汝……下山宿清凉寺,山雲水月,夕景尤嘉……癸酉得風穴賦聯書二通,一投穴中,一焚廟上。八景詠成而雨,數日前山行所無也。簑笠出柏林東,歸蒼谷。甲戌下娥眉,謁蘇墳,還扈澗山堂……』由此可知,今所見《嵩陽觀》《三祖菴二首》《過山書清凉寺》《嵩游途中懷友人五首》等,應該都是這次游嵩時所作。該文最後說:『向使官程促迫,惡能暇豫如此?若非以母病乞休,又惡能有此行耶?山行得詩或寫之石,或書之壁,乃同尾其後一一錄歸。遂令分體集之,得若干首,並紀其游覽始末如此。將時供臥游或同志者賦之云。九月二日蒼谷王尚絅記。』我們或許可以認為這篇《嵩游記》就是詩集《嵩游集》的序言。
十五年之後,再次游嵩,並寫《興復嵩陽書院題名記》,其中云:『乃若書院之盛,則茫無從考。已往正德乙亥,絅嘗撫而詠之,裴徊三嘆。十有五年,今復載興,前堂後祠,垣宇周章,輪奐翼飛,木石耀彩,山若增之而崇者。敦古崇教,侯君之良可知也。』
對佛教名刹風穴寺,王尚絅傾注了大量的筆墨,留下了许多文字,既有賦,又有詩及散文。《風穴》和《風穴寺八景》等詩表達了對歷史人物的追慕之情,如《風穴》中寫道:『蒼谷西來風穴寺,十年塵海動相思。轉憐休暇緣多病,喜得登臨漫賦詩。鑿洞雲峯尋辨叔,聞笙嵩嶽憶庭芝。寂寥汝潁鐘靈地,秋雨嵐亭負愧時。』《風穴問答》闡發了其哲學思想。《風穴賦》引经据典,气势磅礴,曾被黃宗羲選入《明文海》。
此外,《過輔城寺偶題》(卷三)云:『城父何年寺,龍山此日遊。地形分漢楚,天塹自春秋。路古河流斷,祠荒草樹浮。問津思責沈,定鼎憶尊周。』不但勾勒出寶豐重要的地理區位優勢,而且反映了其悠久的歷史人文傳統。組詩《父城懷古四首》(卷六)對歷史的興替深表感歎和惋惜。如其一寫道:『楚王宮殿昔聞名,遺址分明此父城。牛羊落日隨耕豎,不見笙歌作隊行。』其三曰:『龍山地聳麒麟臥,龍水天廻翡翠光。突塚已知無魏主,荒城那復問莊王。』其四為:『孤城一片沒蒿萊,白露青春幾度廻。歎世重收今日淚,知音遙起後人哀。』對歷史的追問溢於言表。
王尚絅歸鄉後,隱居在蒼谷山和密止堂長達十三年,其间既有憂傷和鬱懣,又有閒適和歡樂。對此,詩文都有如實的記錄和表現。如:『種樹蒼山中,中山苦乏水。石磴轉崎嶇,抱甕日爾爾。垂枝嘉果成,露沾亦已喜。山禽虛着眼,山人不蒙齒。』(卷二《山中懷華泉四首》之四)『山中饒勝事,饑餓失所之。奈何秋風顏,將擬盛年時。負疴理毫素,玄髪竞如兹。撫心詎怨老,嗟來謝世疑。感君一斗米,腆贈遙相持。』(卷二《避客山中二首和陶飲酒韻謝李少叅惠米》)反映了山居生活的艱苦與愜意。如卷四《扈澗山莊四景八詠》之《春》写道:『春來結舍碧流灣,病怯柔軀喜燕間。出郭未能三十里,開窗已得萬重山。愁深花鳥知詩興,醉舞松風散酒顏。搔首北堂纔咫尺,斑衣夢裏幾廻還。』《奉祖母祭掃》(卷六)詩中說:『當年山水渾相似,去歲紅芳更不同。何幸白頭隨二母,親扶藍輿到山中。』回憶了自己陪伴祖母和母親到山中祭祀祖先的快樂。《寄弟尚明》《別妹》(卷三)二詩則表達了對兄弟與妹妹的深切思念。前者寫道:『蟋蟀聲初咽,鶺鴒意轉傷。流年驚自改,塵海為誰忙。荆樹春風院,萱花舊日堂。遙憐拜嘉慶,團坐少星郎』;後者說:『長懷于氏妹,返棹下通州。老母三年隔,孤兒萬里愁。身危看佩劒,病起倦登樓。心事憑誰說,封書抆淚流。』手足、兄妹親情,充溢於字裏行間。
王尚絅自己身體多病,妻子早逝、次女和小兒子相繼夭折。這些不幸遭遇在詩文中都有所反映。如:『心病幾番愁肺病,年華十度客京華。每將水火烹粟米,閒看兒童撲柳花。』(卷四《病中六首》之四)『落葉漂泊御苑東,傷心南鴈阻廻風。天涯何處上池水,疾苦無能問病翁。』(卷六《赴浙途次漫興四首之一》)。『天班與爾並馳名,玉女金童作隊行。四十餘年同火伴,不應先我上瑤京。』(卷六《題安人小像二首》之一)『冠簇明珠垂翡翠,褥開文錦繡芙蓉。誰知此語竟成哄,贏得丹青畵爾容。』(《題安人小像二首》之二)『癊疹如何兩度攻,天將毒手賜兒窮。藥吞犀角恰逢滿,卦擲金錢已落空。棗栗猶聞前日語,衣鞵愁檢舊時紅。阿孃夢覺魂如斷,聽說形容在眼中。』(卷十一《仲女澄媛殤葬小誌》)『彭何長,殤何短?天本幽,神理漶。繄疇愬疇斯,斷母兮,亡父兮,患兒苦饑,兒苦痺。聽兒哭,焦以懣。兒不亡,羗孰管彭殤殊高下,散兹焉,齊莊其誕!』(卷十一《小五哥寄瘞誌銘》)這些詩文記錄了王尚絅妻子早逝、亡女喪兒的悲慘遭遇和痛苦之情。
王尚絅在長期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對文學藝術規律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和總結,形成了鮮明的文學主張。一是重視詩歌與現實的關係,主張詩歌要言之有物,切於世用。在《鳳巢小鳴稾題辭》(卷九)中說:『嘅自詩亡道敝,則所謂詩者亦物爾,玩焉喪志。……工如漢唐,工矣而愈敝;宋無詩已而道存。則所謂詩者,于此乎?于彼乎?虛車窾櫃,將傳邪彰邪?使人繼其聲邪?《易》稱有物,《傳》戒不倫,信而有徵者,君子與!夫聲莫有精於此者也。勸善懲惡,移風易俗,感天地,動鬼神,理萬物,何物也而可以虛飭哉!君子顧何靳而不為?不曰藉詞以鳴意,託興以鳴志,引物連類以鳴心乎?不曰因風有聲,而其聲又足以感物乎?』王尚絅認為,詩歌要『勸善懲惡,移風易俗,感天地,動鬼神,理萬物。』而把那些空洞無物的詩歌比作『虛車窾櫃』,一無所用。
二是強調文章的神韻,主張文以神為主。他在回顧自己多年的創作實踐後指出:『世之論文者必曰文須學古,臨文則曰某學某,某學某。某操鉞伐柯,十年不就,洎病伏蒼谷,收視反聽,無意於斯文也久矣。乃翰林主人偶爾相示曰:「文,心之神也。」既而得提學清逸先生文稾二函,日夜讀之,劃然嘆曰:「斯文信乎其神矣哉!」蓋嘗思之:夫有心矣,苟非神以主之,辟則走碑行尸,種種皆迷,安在其學古人也?雖學且成,亦土木之形爾。夫惟神焉天君,麾指所向,是道思或起之,得若相之。其來也,猶泉湧;其行也,猶響應。形生神發,化之無窮。……弟尚明曰:「眉山謂文章以氣為主,伊洛謂文章主於理,然則何居?」嗚呼,知先生之神者,理與氣可得而言矣。羲文禹象,所以發造化之秘者,非神而能此?請質之先生,以為何如?』(卷九《讀清逸文稾題辭》)在三蘇強調『氣』、二程強調『理』的基礎上,王尚絅主張要以『神』統『理』與『氣』,强调文学的神韵,唯有如此,才能使文章『猶泉湧』『猶響應』,『形生神發,化之無窮』。
二
明代著名學者薛應旂指出:『(蒼谷)先生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有《蒼谷集》十二卷行於世,然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兩程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而開來學者。』[十]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孫奇逢在《中州人物考》中將王尚絅列入『理學』人物,與何瑭、崔銑和王廷相等並列。[十一]
王尚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其理學成就表現在客觀評價二程在理學上的貢獻,自覺維護二程及其學說的地位,表彰理學先賢,直承張載『氣一元論』思想,認為各種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成都是由『氣』及其變化決定的,豐富了明代中期的『氣本論』理論,重視孝道和夫婦之道,強調『養心』教育,提出了個人修養的標準和典範。
王尚絅『遠宗二程』,自覺維護『二程』及其學說,是其堅定的立場。一方面,他實事求是地總結和評價『程氏之學』,回顧了孟子以後中斷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儒學發展軌跡:『嘅自羲皇堯舜,世歷周孔,治亂相乘,以勳以報。軻死亡傳,糜爛六籍,湮沒千載,發明於程氏兩夫子。……夫子吾不得而見其聖人否也,方其年有十五已志乎聖人之道,非聖者無學焉。涵養曰敬,踐履曰誠,進學曰致知,篤信行果,守兹靡渝。求於內而不荒於外,亟於本而不眩於末,止於道而不狃於異端。微於獨,顯於身;徵於言,發於事功而不違於天地,不疑於鬼神,不戾於天下,不悖於萬世,不詭於聖人者,是謂程氏之學。』(卷十《汝州聖學書院碑銘》)這些極為深邃而準確的概括,高度評價了二程的學術貢獻。
另一方面,堅定維護二程的歷史地位。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汝州知州張崇德創建三賢書院,請王尚絅題寫書院碑銘,由於在『三賢』人選上意見的分歧,他連續三次致信張崇德,據理力爭,堅决維護二程的地位。第一封信中說:『夫所謂三賢云者,初不識其為誰,既而閱狀云伊川、東坡、潁濱,而不及明道。考之明道,始終在汝,東坡始終未至,潁濱史志皆無所載。今曰三賢,襲之古耶?創諸今耶?襲之古,則據自何典?創之今,則起自何義?余皆不識其何說也。……庶昭今傳遠,或者亦周公孔子之道也。』(卷九《汝州書院第一議》)強烈建議對方解釋確定伊川、東坡和潁濱為『三賢』的歷史和現實依據。第二封信認為:『書院曰三賢者,黃君狀謂程氏伊川、蘇氏坡、潁。曰兩賢,絅主明道、伊川言也。葢程氏本河南人,明道自監察御史里行監近鄉酒稅,光庭歸自汝上,有春風之想,召命及門,而卒於汝。伊川授汝州團練推官、經筵坐講,被劾編放還,范祖禹議復汝上田二十頃,則汝固兩賢歌哭之所、游息之鄉也。和風化雨,熏潤猶存,從而祠之,孰曰非實錄哉!……今以義起所可者三,所甚不可者二:耑祠二程可也,耑祠二蘇或可也;併出三賢,特祠明道亦可也。……如前所謂三賢者,像列一堂,甚不可也,而又獨黜明道,則又甚不可也。……是故寧得罪於蘇,孰可得罪於程?得罪於一人,孰可得罪於君子?得罪於一方一時,孰可得罪於天下後世?』(卷九《汝州書院第二議》)闡明了自己的堅定立場和鮮明觀點。
為了維護理學傳統,王尚絅積極保護、禮敬理學先賢,其中對李希顏事迹的弘扬用力尤多。《明史》卷一百三十七載,『李希顏,字愚菴,郟人。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之,至京,為諸王師。規範嚴峻。諸王有不率教者,或擊其額。帝撫而怒。高皇后曰:「烏有以聖人之道訓吾子,顧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贊善。諸王就藩,希顏歸舊隱。』[十二]《明史》對李希顏事迹記載簡略,王尚絅通過深入挖掘,為李希顏樹碑立傳、建祠祭祀。如稱李希顏『學淵伊洛,遙出東魯,……性行峻茂,貫酣群籍』,『立朝風節巋然,傳聞海宇』『道窮根柢,期於力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懷信守度,孤介寡合,卒忍煢以死……乃下無所舉,而上焉弗詢,觀風弔古,心兹名教者,其可歎已!平生著述,諫草、詩文散逸,所及見者《大學中庸心法》』。(卷十《皇明經筵講官左春坊贊善大夫愚菴李公墓碑銘》)並進一步贊道:『先生以我朝帝王之師,高前古夷齊之行,名重高皇,禮勤徵聘,垂勳國史,進講經筵。著述闡性理之淵,存省造聖學之粹。考平生之履歷,關宗社之污隆。』(卷十二《祭先賢李愚菴文》)這一系列著述,有利於我們全面認識李希顏,了解中原理學的發展概況。著名明史专家黃雲眉先生在《明史考證》『李希顏傳』中曾指出,本傳可參閱王尚絅《蒼谷集》所撰希賢墓碑銘。[十三]充分肯定了其文獻價值。
二是豐富發展了『氣本論』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明代中葉以後,『氣學』思想得到了空前發展,王尚絅的『氣學』思想,是明中葉『氣本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氣』决定風的形成和變化。他說:『聞風氣為之,天地之號令也。必五行得令,四時順序,而後八方風各應律而至,以成歲功,否則變怪百出,不可具狀。然有正有變,皆氣之為也。』(卷一《風穴賦序》)在談到『氣』的變化對風的影響和决定作用時,王尚絅指出:『陰得陽而為之風,氣變而風亦變。故風從風曰巽,風行地上曰觀,風行天上曰姤,風行山上曰蠱,風行水上曰渙。於四時曰春曰夏,仁氣為之也;曰秋曰冬,義氣為之也。若乃冬風暴,秋風災,義氣之戾也;夏風欬,春風猋,仁氣之戾也。』(卷八《贈張子風序》)
第二,自然界和人類的各種不同現象都是由『氣』的變化形成的。他說:『氣之所化,飛物之所本。有正有變,互為消長。或自南而北,或自北而南。自北而南,氣正矣,則其鍾於物也,為陽,為剛,為慶雲,為時雨,為君子,為祥瑞,為鸞鳳,為芝草,為靈椿。人得之則為福,為壽,為聰,為明。自南而北,氣變矣,則其鍾於物也,為陰,為柔,為冰雹,為暴雨,為小人,為魍魎,為鴟鳥,為荼毒,為臭草,為怪物。人得之則為胗,為蔑,為癱,為夭折。或隨地而殊,或應時而變,故曰氣為之也。』(卷十《風穴問答》)質言之,互相矛盾着的『正氣』與『變氣』,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其間的消長變化,不但產生了自然界的陰陽、剛柔、慶雲、時雨、冰雹、災害等互相對立的現象,而且還决定了人的福壽、夭祥、善惡、賢愚、美醜等,『氣』的不同運動形式是構成不同事物的基礎。這種認識包含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王尚絅認為人生命的長短也是由『氣』决定的,他說:『自有生以來,安有所謂不死人哉?蓋命之修短,各懸於氣之稟受,而不繫於人之修為。』(卷九《陳圖南蛻骨成仙辯》)他指出,上古之時,人的壽命長,是因為那時天地之氣厚;而後來隨着天地之氣變薄,人的壽命也就變短了,因此世上沒有長生不死之人。他對世人希望長生不死的愚昧行為和術士異端危害社會的不良現象進行了嚴肅批判,斷然指出:『仙家幻妄,……使世人絕欲導氣,貪生妄想,卒之尤速其死者。首駢踵聚,禍不甚邪?』(卷九《陳圖南蛻骨成仙辯》)體現出了唯物主義思想。
第三,認為陰陽二氣的相互作用產生世界萬物。這種觀點充分表現在其《名四子說》一文中。該文認為,『氣』雖然分陰陽,但陰陽二氣的『和合』,也即相互作用,形成了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進而引起世界的千變萬化。基於這種認識,他分別給四個兒子命名為同、和、爻、府,貫徹了陰陽二氣『和合』的思想。
三是在倫理道德建設方面卓有建樹。首先是『忠孝論』思想。王尚絅說過:『進思盡忠,退思盡孝,此生人之大義,無所逃焉者也。』(卷七《復除再陳疏》)『進思盡忠,退思盡孝』,是其處理君臣、父子關係的基本準則。當他得知祖母與母親病重時,立即上《陳情乞養親疏》,請求歸養二母:『臣祖母李氏見年九十一歲,臣母聶氏六十六歲,老病尫羸,不離床褥,聞賊驚恐,舊疾愈重,思欲一見臣面。臣聞命傍徨,無以為計……臣奔父喪,未能親自裹斂,洎今抱恨,母且老病,迎養維艱。棄親供職,已復六載,當風燭垂燼之餘,遭兵火流離之禍。思臣自孩提為祖母鞠育以有今日,此里巷所共知者。自登科授任,與母氏相違,動無寧歲,晨夕寤寐,淚漬衾枕,展轉自省,狼狽為多。况今流賊汹湧,往復猖獗,倘母有不測,臣將何為!雖生無以報國恩,雖死無以入家廟矣。』(卷七《陳情乞養疏》)他以未能為父裹斂而內疚,倘母再有不測,罪責難辭。為此,不等批復即决然旋歸故里,侍養二母。其友王龍湫贊道:『以二母垂老,引疾抗疏,未報而行。……攜家以還,率配靖懿周氏子具菽水盡李太君、聶太安人歡。』(王綖《明故浙江右布政使蒼谷王子墓誌銘》),『棄官赴母難十九年,薦徵累不就,竟卒于官,可以知孝。』(王綖《明貞孝文子王公靖懿君周氏墓表》)
王尚絅認為夫婦關系至重,是『人道之始,王化之端』。(卷八《哀聲集後序》)他認為孔子刪《詩》即體現了重視夫婦之道的思想。因此,他堅守夫婦之道,當妻子亡故後,他在妻子靈柩前鄭重承諾:『絅嗣今而後,當益勵清貞,益堅苦節,完兹德音,以終我安人之意。教爾五子,各俟成立,撫爾二女,各成婚姻,以終我安人之業。養終老母,送終爾父爾母,以終我安人未泯之心。是絅所以報忠良而終餘生者,如斯而已矣。兹當七七,親眷咸在,謹與安人盟諸柩前,神其用妥。如或少違初志,靈其鑒察。』(卷十二《祭亡妻安人文》之二)决心以實際行動踐履自己的承諾,盡到丈夫的責任,維護夫婦之道。
王尚絅非常重視倫理道德的『養心』教化作用。他說:『社五土,稷五穀,神司之,養人之身者也;人倫之教,孔子司之,養人之心者也。人莫大於心死,而身次之。土穀不可一日而亡,則孔子之教,顧可一日而亡於天下也哉?』(卷七《重建虎亭文廟記》)他強調身心兼養,而且養心重於養身。他特别強調書院在造就道德之士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庠校以儲文學登用之才,書院又以養性命道德之士』(卷九《汝州書院第二議》),書院的重要職能在於使『有司於以專祠先師,以緣升道德之士,以端士向,以建民極,以隆化本』。(卷十《汝州聖學書院碑銘》)
王尚絅自律甚嚴。他說:『進退出處,維聖有訓,落魄如稽阮數子者,非孔孟之徒所敢道也。』(卷十二《謝王巡撫俞巡按會薦書》)他通過列舉江革、薛包、王祥等歷史人物在『孝』『德』『仁』『義』『敬』方面的感人事蹟,确立父子、君臣、夫婦、朋友等倫理關繫的標杆(卷十《明倫銘辭》);還從衣服、飲食、義利、憂樂、敬誠、儉奢等方面提出了修養的途徑(卷十《敬身銘辭》)。他身體力行,『一步一趨,悉中道規。……造詣精粹,拔俗自持。邃于理學,後世是師。』(《明故浙江右布政使蒼谷王子墓誌銘》)
王尚絅的理學成就一方面靠自己的努力修為,『自童稚時已立志為聖賢之學,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邃三禮』(孫奇逢《王布政公傳》)。另一方面得益于師承陳雲逵。明代理學家馬理在談到明代理學發展時指出:『夫古今諸賢之學,各有所發,宋之理學,皆發于陳摶、濂溪、康節二派是已。對山發於教諭趙內江,後渠發於甘泉學官李子乾,涇野發於蜀人高學諭,大復發於高鐵溪,蒼谷發於陝州陳監丞。……陳監丞者,誦先王先聖之法言,身體而力行者也。……陳子居處莊,禮樂日不去身,……陳子一世之英也!但位卑而時人不知,蒼谷乃獨知而友之,取其益焉,他日文行名世,……然得於輔仁之益之深,則陳丞子也。』(《蒼谷全集》馬理序)陳監丞即陳雲逵,明代陝州人,字中夫,曾為蘭州學正,以經術六藝造士,後為國子監丞,理學造詣極深。王尚絅《輓監丞陳先生》一詩寫道:『嵩山陰繞重雲結,河水東流夜嗚咽。儒林梁棟風摧折,尼父袂掩麒麟血。游楊門外空愁雪,三禮殘編復斷絕。憑誰更補冬官缺,長歌一聲天地裂。』對陳雲逵的成就贊歎不已,对其去世深表悲痛和惋惜。
作為著名理學家,王尚絅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明人薛應旂認為:『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而開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哉?……余為南吏部主事時,安陽崔後渠先生為禮侍,嘗與余論弘治人才在其中州者,則以何柏齋、王蒼谷為首,稱謂其志于理學。』[十四]清人劉宗泗說:『尚絅學問淹博,雅善詩文,然實非所好也。當時推理學者,每與何文定瑭同稱云。』[十五]其豐富的哲學思想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三
截至目前,現代學者對王尚絅的研究,在文學研究方面除廖可斌、黃卓越等先生的有關論著,有張長法先生《王尚絅及其文學創作》[十六]、葛澤溥先生《王尚絅和他的詩歌創作》[十七]兩篇論文,以及楊輝的碩士學位論文《王尚絅年譜》[十八]。在哲學方面有本書作者的《王尚絅理學思想論綱》[十九]一文。
為全面考察明代的文學與理學,推动優秀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我們决定在學界已有成果基礎上,整理出版王尚絅文集,以期推進王尚絅研究。
王尚絅文集國內主要有兩種版本:一是明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王綖編、王同刻本《蒼谷集錄》,十二卷,現存六卷,藏於國家圖書館。
二是清乾隆二十三年(一七八五)王純『密止堂』刻本《蒼谷全集》,十二卷,附錄一卷。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和河南大學圖書館等有收藏。北京出版社將其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出版。
三是清同治年间刻本,與乾隆刻本稍有不同,对王尚絅的轶闻材料有所增補,其著作未有增减。河南新鄉市圖書館有收藏。
本次整理以乾隆二十三年『密止堂』刻本《蒼谷全集》為底本,主要參考以下資料:
《蒼谷集錄》,国家圖書館藏王綖編、王同明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刻本(以下简稱明本);
《盛明百家詩·王方伯集》,齊魯書社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浙江省圖書館藏明嘉靖至萬歷刻本;
《直隸汝州全志》,清白明義編,一八四〇年刊本。
明嘉靖八年《登封縣志》,登封縣縣志辦公室一九八四年重印本。
清同治三年《郟縣志》,郟縣志總編室一九八三年標注排印本
清道光十七年《寶豐縣志》,寶豐縣史志編纂委員會,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清同治辛未《葉縣志》,葉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風穴志略》,任楓輯,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影印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本次整理,在校點基础上,对部分人名、地名及词语加以簡要注釋。
參考文獻:
[一]清同治三年《郟縣志》,第四七九頁,郟縣誌總編室標注,一九八三排印本。
[二]同上書,第二七二頁。
[三]同上書,第二七三頁。
[四](清)何景明《大復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五](清)何景明《大復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廖可斌:《求索》,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七]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八七頁。
[八]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九七—九八頁。
[九](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第五〇一六—五〇一八頁。
[十](清)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六,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三四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第二九五—二九六頁。
[十一](清)孫奇逢:《中州人物考》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十二](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第三九四九頁。
[十三]黃雲眉:《明史考證》,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一七五頁。
[十四](清)《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六,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三四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第二九六頁。
[十五](清)劉淙泗:《王布政尚絅》,《蒼谷全集》附錄。
[十六]張長法:《王尚絅及其文學創作》,《鄭州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十七]葛澤溥:《王尚絅和他的詩歌創作》,《平頂山學院學報》二〇一〇年第三期。
[十八]楊輝:《王尚絅年譜》,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二〇一六年。
[十九]王冰:《王尚絅理學思想論綱》,《中州學刊》二〇一三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