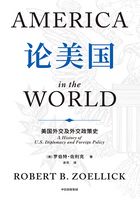
第2章 《美洲新纪元·大陆领土 财政权 中性独立以及共和党人联盟(1789—1897)》:以经济和金融构建权力体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选择美国的第一位财政部部长
1789年4月,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前往纽约市参加就职典礼。中途在费城逗留时,华盛顿找到了他的老朋友——曾经担任过美国革命政府财政总监的罗伯特·莫里斯。莫里斯是这个国家最有势力的商人兼金融家,华盛顿的大陆军陷入最低谷的时候,正是他出资使这支军队得以坚持下去。莫里斯曾经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盟友,他甚至还曾经以个人身份贷款支付军队开支、资助武装民船、购买武器和收买间谍。
根据华盛顿的继孙在多年后写下的资料,当时华盛顿邀请莫里斯出任新一届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莫里斯拒绝了这一提议,可能是因为他需要集中精力解决个人的财务问题——他后来正是因财务问题而破产的。不过,莫里斯给了华盛顿一个建议:“我可以推荐一个比我聪明很多的人来担任你的财政部部长,这个人就是你以前的副官汉密尔顿上校。”华盛顿听了后很吃惊,他说自己从来都不知道汉密尔顿“还懂财务”。[1]
汉密尔顿1777年初当上华盛顿将军的副官时,年仅22岁。在8年的战争过程中,大约有32名副官曾在华盛顿的指挥部里工作过,但是汉密尔顿在这些精英中属于出类拔萃的那一个。1789年,汉密尔顿才30岁出头。在新宪法的草拟和修改过程中,这位纽约人曾是莫里斯的盟友,但两人并不是关系很亲密的朋友。在向华盛顿推荐汉密尔顿之前,莫里斯似乎并没有跟汉密尔顿打过招呼。[2]
青年战略家
莫里斯知道汉密尔顿的头脑有多么聪明,也知道这个年轻人对工作有着巨大的热情。1781年4月,也就是国会任命莫里斯为财政总监后不久,汉密尔顿就主动写了一封自荐信给年龄比他大,经验也远比他丰富的莫里斯。信是用打字机写的,长达31页。当时汉密尔顿已经辞去了华盛顿副官的职务,退隐到他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的藏书室里,并在那里思考美国的国家大事。他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构思出了一套关于财政、国家权力和战争的新思想。这封长信实际上是对之前两封分析政治和金融问题的信的提炼和延伸,其中一封是汉密尔顿在1780年写给国会议员詹姆斯·杜恩(James Duane)的,另一封则可能是他在1779年写给斯凯勒的。这三封信不仅勾勒出了解决战争问题的计划,也为年轻的美国设计了一套财政和经济权力的体系。[3]
汉密尔顿见证了一支军队所接受的考验,也见证了更加重要的、一个新生国家所接受的考验。两者都曾饱受资金匮乏之苦。军队发不出军饷,买不起军装,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他们缺少武器和弹药。一些原本像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一样的战场勇士最后沦为叛徒,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钱。汉密尔顿在给杜恩的信中说,军队已经成了乌合之众。在1780年写给好友(也曾担任过华盛顿的副官)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的信中,汉密尔顿沮丧地断言:军队、各州政府和国会都在“一大群傻瓜和无赖”的掌控之中。汉密尔顿在另外一份文件里承认,缺钱可能导致军队解散或丧失战斗力,从而使民众转而呼唤和平。[4]在某些情况下,绝望的军队甚至有可能在指挥官的率领下掉转枪口,瞄准那些对他们表现出漠视或鄙视的政治家。
然而,汉密尔顿在写给莫里斯的信中所展现出的视野,已经远远超出了战场和军营的范畴。他上升到战略层面,分析了美国和它的敌人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汉密尔顿认为,英国和美国正在打的是一场消耗战。他分析了英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位上校总结道:美国要想取得胜利,不仅要充分调动美国的资源,还要削弱英国政府的信用和意志。[5]
杰出的汉密尔顿传记作者罗恩·彻诺(Ron Chernow)写道:对于汉密尔顿上校来说,“革命是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实践车间”。[6]汉密尔顿最重要的洞察在于,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良好的信用,才能承担一场长期战争的开销。简言之,国家需要为战争买单。“没有收入做基础的权力就是泡沫。”汉密尔顿总结道。
1781年,汉密尔顿拒绝了新任财政总监莫里斯发出的共事邀请,也没有进入国会辅助莫里斯。他选择去大陆军担任前线指挥官。他领导了来自纽约的一个营,并在随后的约克镇战役中攻下了两个英军主要堡垒中的一个,帮助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中最后一次重要战役的胜利。汉密尔顿孜孜追求荣耀和声望。不过,与其他军人不同的是,他理解财政和经济活力对国家权力和复原力的重要性。
汉密尔顿对战略、政治和财政的洞察,促使他产生了制定一部新的全国宪法的想法。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之中,汉密尔顿倡议修宪,他阐述了财政、政治体制以及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此外,汉密尔顿在设计财政和政治制度时也考虑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具体的外交行为。《联邦党人文集》直白地指出,在《邦联条例》之下,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弃儿国家。要想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取得成功,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对外贸易、稳健的货币、政府收入和一支常备军队。另外,美国人倚重海上贸易,所以美国也需要一支海军。[7]
汉密尔顿的经济战略
富兰克林签署的《巴黎条约》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赢得了大片领土。杰斐逊领导下的弗吉尼亚人开始认同这样一种理念,即土地是财富的来源、自耕农们获得自由的基础,以及国家安全的空间。汉密尔顿则明白,美国要有财政实力、流动资金和经济制度作为保障,才能拓展自然疆界。
美国的第一位财政部部长欣赏英国威廉·皮特父子(William Pitt the Elder and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的政策,也佩服英国政府设计的财政体制。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后来认为汉密尔顿是以英国为榜样,但在应用于美国时又做了调整:英国设计的是一个为了给政府筹集资金的体系——这可能偶尔会带来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副作用——而汉密尔顿的体系则是用财政手段去满足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需求。汉密尔顿想要解决一个难解的财政问题。与此同时,这位新任财政部部长也在为美国的权力设计一套新的架构。[8]1789年的国庆日,汉密尔顿为他的前同事和战友纳瑟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将军写了一篇颂词,其中也顺带提到了未来的工作,汉密尔顿解释说,他的任务是“[建立]美国伟大的上层建筑”。[9]
汉密尔顿年轻时,曾抄录过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演说集》中的一段,这段话体现了汉密尔顿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欲:“[领袖]要知道的不是事件发生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而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制造出事件。”[10]汉密尔顿会驱策自己做出决定,而不是等着“查收邮件”或召开会议来安排他的行动。而且,汉密尔顿的各种不同举动都符合他的整体计划。作为一个管理者,汉密尔顿会从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的三卷本回忆录中寻找启示,后者是法国路易十六时期备受尊崇的财政大臣。内克认为,一个伟大的部长必须有能力“既了解整个系统,同时也了解系统内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11]
其他人已经论述过汉密尔顿为信贷、国家银行和制造业做出规划的历史,我想把重点放在汉密尔顿规划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的互相配合之上。汉密尔顿的偿债体系使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成为一个良好且可信赖的信贷产品。由此,包括联邦债券在内的各种证券扩大了这个新生国家的货币基础,带来了可用于投资的流动资金。新成立的美国银行改善了联邦财政,拓宽了私人信贷体系并支持投资。在政府偿还联邦债务的过程中,金融和商业资本也从新政府的成功之中分得了一杯羹。联邦政府对国债承担偿还义务,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大的支持力量并扩大了信贷基础。新的收入系统,尤其是“温和”的关税,将税收和利息支付联系到了一起。“偿债基金”的设立让联邦债券的投资者们更无后顾之忧。汉密尔顿还建立了新的海关机构(海岸警卫队)和信息系统,这显示出这位财政部部长不仅有能力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定规划,也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执行能力。通过上述举措,汉密尔顿得以降低偿债利率,并通过海外债券募集更多的资金。此外,就像汉密尔顿在给莫里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只要不过度发行,国债就是国运。它会成为我们国家的强力黏合剂。”[12]
麦克唐纳教授指出了汉密尔顿规划中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部分:维持良好的信用既需要现实条件,也需要市场心理,也就是信心。汉密尔顿相信,新政府必须快速采取行动,才能获得公共债权人的信心。[13]汉密尔顿还认识到,美国的外交将会有助于建立这种信心,也有助于新创建的政治经济体系在实践中取得成功。
外交战略配合经济计划
汉密尔顿进入外交领域的时间甚至早于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后来的一些国务院权力捍卫者把汉密尔顿的外交行为视为越权。[14]实际上,汉密尔顿的外交行动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从一开始就包含了经济判断与利益考量。这种做法一开始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则变成一种不失时机的主动选择。
在汉密尔顿看来,美国在陆上和海上两方面都有成为强国的潜力。任何在美国实行孤立主义的幻想都是愚蠢的,因为美国是泛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欧洲列强在欧美两块大陆上都想取得优势。在制宪会议期间,汉密尔顿呼吁建立一个更强的国家政府,与“认为大西洋可以保护美国免受未来冲突困扰的幻想”针锋相对。[15]
汉密尔顿认识到了在权力政治中维系平衡的基本原则。欧洲霸权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需要防止欧洲大陆列强勾结起来控制密西西比河流域,还要提防这些列强引诱西部领土各州及其土地之上的拓荒者们,削弱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
密西西比河流域是北美的战略权力心脏地带。在18世纪90年代,这一地区仍是一个多方争抢的缓冲区。汉密尔顿想把西班牙赶出北美东部,并且把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纳入美国版图。这位财政部部长很担心法国——无论是君主制时期、革命时期还是后来的帝国时期——对北美土地的觊觎。汉密尔顿甚至还认为头号海上强国英国也许会帮助美国,阻止法国和西班牙在北美土地上对美国的遏制。汉密尔顿相信,美国假以时日肯定会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成为强国之前的过渡期,这个国家需要巩固跨大西洋贸易,保持内部凝聚力,开垦西部土地,夺取密西西比河流域,并维持住荷兰和伦敦的那些银行家的信心。[16]
汉密尔顿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需要帮助国内维持和平和稳定,从而为国家积蓄力量。他也有一些现实的短期目标:结束与美国原住民的敌对状态,阻止欧洲人对此类冲突的鼓励;迫使英国人撤离他们在美国西部土地上仍然占领着的要塞;从进口贸易中获取收入,以支持新的信贷系统。1794年,联邦收入的约90%来自贸易关税,其中从英国那里获取的贸易收入占美国进口收入的近四分之三,占美国出口收入的二分之一。[17]美国同样需要来自英国的贷款。
与英国的战略对话?
1789年10月,刚刚就职不久的汉密尔顿就向乔治·贝克威思(George Beckwith)阐述了他的外交战略,贝克威思是一位英国陆军少将,也是英国驻北美总督多切斯特勋爵(Lord Dorchester)的助手。贝克威思是以非正式使者的身份前来拜访的,他警告汉密尔顿,美国国会实行的新关税政策对英国有歧视,将会招致英国的报复。但是,汉密尔顿则向贝克威思抛出了在一个更大范围内进行利益交换的提议。
如果是在今天,汉密尔顿的外交手段会被贴上“战略对话”的标签。这位财政部部长提出了他对国内和国外形势的看法,他简单地勾勒出了两国关系可能的走向——实际上是他希望的走向。汉密尔顿分析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并将各种政治约束因素考虑在内,对双方的下一步行动提出了建议。汉密尔顿明确指出了没有商讨余地的问题——例如英国撤出要塞,以及阻止北美原住民缓冲区的建立——同时还提出了其他要求,例如归还战后随英国军队一起离开的奴隶等。他避免指责对方,而是尽量解释自己的意图,并探寻双方利益一致之处。
汉密尔顿观察到,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正好与制造业突出的英国形成互补。美国人的购买力已经十分可观,但还会增长。英国可以判断出美国的影响力将会增大,因此,英国政府与美国不仅应该建立商业联系,也应该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但是,汉密尔顿强调:要想形成利益共同体,英国就必须尊重美国。这个由前英国殖民地组建的国家虽然曾在英国政策的迫使下与法国结盟,但美国人还是更喜欢和英国建立联系。“我们用英语思考”,汉密尔顿对贝克威思解释道,其实他的法语也很流利。汉密尔顿警告说,如果遭到英国的藐视,美国就会与法国结盟,并因此威胁到富饶的英属西印度群岛。[18]
在经历了8年的苦战之后,汉密尔顿对曾经的敌国亮出的这番开场白令人吃惊。相比之下,杰斐逊和麦迪逊都还保持着对英国的敌意,他们都想无视傲慢、腐朽的“英国雄狮”,转而寻求发展与法国之间的关系。1791年底,乔治·哈蒙德(George Hammond)作为英国驻美公使抵达美国,但杰斐逊却坚称两人必须以书面形式沟通。不久之后,这个外交渠道就引起了一场争吵,双方围绕着谁先破坏了和平条约的问题展开辩论,并由此在一系列问题上互相指责。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的观点是幼稚的,外交手段也是不切实际的。
实际上,汉密尔顿的提议意味着加入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甚至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向英方倾斜——前提是英国停止威胁美国在北美的利益,并通过一个商业条约与美国展开经济上的合作。汉密尔顿认为,美国这个新生的商业伙伴终将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美国和英国维持紧密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1782—1783年,曾经同意与美国议和的英国首相谢尔本勋爵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富有远见的英美合作草案。但是,英国对美国的敌意还是太浓,而且谢尔本政府随后也下台了。与之类似,汉密尔顿的提议——与英国建立泛大西洋“特殊关系”——也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被美国公众所接受。[19]100年后,正如汉密尔顿所预见的那样,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强国,而英国则在设法满足美国人的需求。
中立政策
汉密尔顿对英国的开场白没能奏效。法国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也威胁到了欧洲的安全和美洲的稳定,而汉密尔顿设计的新制度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因此,这位财政部部长提出了一项外交原则,也就是中立主义,这项原则主宰美国外交超过一个世纪。中立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它的应用过程。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两人就美国遭到侵犯时应该“亲法”还是“亲英”展开辩论。中立政策有时会惹恼那些为重大利益而战的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冷战时期,美国有时会反对那些声明中立的国家。
在英国人的掠夺行径面前,汉密尔顿劝说华盛顿总统“在坚守国家尊严的前提下,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他担心战争将会“从根基上斩断美国的信用”,打击出口,扼杀进口和税收,从而导致债务违约。反之,只要能保持和平,“环境的力量将使我们能以足够快的速度从贸易中获取所需资金”。[20]
汉密尔顿的中立无疑是偏向英国的,因为美国需要在一个英国主宰的商业世界里发展。巴黎的革命热情威胁到了美国的内部凝聚力。法国经济无法满足美国的需求,汉密尔顿想要跳出过去与法国签订的条约所围成的“囚笼”。他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避免与所有国家产生除商业关系以外的联系”。[21]
18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对美国舰只发起攻击,汉密尔顿再次劝说美国政府维持和平。他反对因为一些传言或“小打小闹”而与法国大动干戈。彻诺总结道,汉密尔顿的处理方式是“充满激情的实用主义”。[22]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美国实力的增长,汉密尔顿的国家陆权与海权互相巩固的思想开始影响他的外交理念。1798—1799年,时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疲于应付与法国之间的“准海战”(Quasi-Naval War)之际,汉密尔顿提议建立一支更强大的海军。他相信,维持和平的最后方法就是做好作战的准备。汉密尔顿设法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常规陆军,由华盛顿担任总指挥。他甚至还考虑过与英国和皇家海军合作,逼迫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让给美国,从而预防这些领土落入法国人的手中。[23]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和对同盟的警告
在乔治·华盛顿1796年发表的告别演说中,汉密尔顿的外交思想得到了集中的表达。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紧密合作,共同完成了这份讲稿。彻诺观察到,演说中涉及的话题都是围绕着华盛顿对当时一些争议问题的处理办法展开的,其中包括外交政策和国内的一些纷争。这篇告别演说成了美国外交“圣经”的第一章。[24]
从本质上来说,华盛顿演说的主题就是呼吁维护联邦。这位总统列举了一些对联邦构成威胁的因素,并强调了维持一个有活力的国家政府的必要性。汉密尔顿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段话,说明了由财政收入所支撑的政府信用与国家“实力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外交政策体现出了华盛顿的经验和愿景,也就是汉密尔顿的中立路线——在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上,既不要“习惯性仇恨”,也不要“习惯性偏爱”。华盛顿在演讲中还警告美国不要搞“永久同盟”,这句话的影响持续了很多年。杰斐逊后来也做了同样的表态,说要提防“纠缠不清的同盟”。美国人对同盟的敌意成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传统。在建国后15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们一直在寻找其他的组织概念,以取代同盟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汉密尔顿的外交方法
汉密尔顿的外交风格是理智的、礼貌的、强硬的,但并不是好斗的。他认为各个国家都会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而行动,但也知道处理国家事务的个人也是有感情的,未必总会在行动中保持理性。一时冲动可能会让官员在计算利益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汉密尔顿喜欢“外柔内刚”的处事态度,与他类似的西奥多·罗斯福把这种风格称为“温言在口,大棒在手”。[25]
汉密尔顿这种慎重的外交风格并不只是用在与英国的关系上。在处理随后的法国入侵事件时,汉密尔顿也警告美国不要反应过激。他指出,“傲慢没有任何好处”,还呼吁美国采取“真正的强硬态度”,“把力量和克制结合在一起”。[26]
与富兰克林一样,汉密尔顿也观察到“鸡毛蒜皮的小情况、小冲突,都可能让人在整体上对一个国家产生好感,反之亦然”。他还发现,“国家有时就像个人一样,会因为对方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事情发生争吵”。汉密尔顿的一位传记作者对汉密尔顿的外交风格做了恰如其分的总结,认为其特点是“坦率、善意和有良好的判断力”。[27]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提出过类似的外交建议:“凡事要分清孰轻孰重。”
塔列朗与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
在基辛格博士对欧洲外交的研究中,夏尔·德·塔列朗(Charles de Talleyrand)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我们可以通过他来对汉密尔顿及其主导的美国外交进行细致分析。1794年初,塔列朗从法国“恐怖统治”之下逃出,以无国籍流亡者的身份在美国居住了两年。这位法国人是一个有智慧、有知识的无赖。塔列朗非常崇拜美国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他甚至还曾写道:“拿破仑、[英国的]查尔斯·福克斯和汉密尔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三个人,而且……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汉密尔顿排在第一名。”塔列朗声称汉密尔顿已经“看透了欧洲”,也就是说,这位美国人已经对塑造欧洲大陆的政治和权力格局的各种力量进行了评估。[28]
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的发展需要长期信贷和工业产品,而最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国家是英国,而不是法国。塔列朗对此表示认同。至于美国和之前的敌人英国联手的难度,塔列朗也赞同汉密尔顿的观点:“一旦你已经赢了,就不会再恨对手了。自豪感既然已经得到满足,就不会再想去报复。”[29]汉密尔顿和塔列朗没有充分意识到,杰斐逊、麦迪逊和其他弗吉尼亚领袖都认为他们和趾高气扬的英国之间仍然有一些恩怨没有解决。
汉密尔顿和塔列朗都对对方的学识表示敬重,在外交政策方面也都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不喜欢感情用事,但他们两人的个性却根本不同。1795年的冬天,塔列朗冒着严寒走在纽约市的大街上,他要去参加一个晚宴。路过华尔街的时候,这位狡猾的天才瞥见汉密尔顿正坐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借着烛光工作。当时汉密尔顿刚刚辞去财政部部长之职。这个法国人对此困惑不已:“我看见一个曾经为整个国家创造了财富的人,正在通宵达旦地为养家糊口而劳作。”此后不久,塔列朗回到法国担任外交部部长,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可要利用这个工作机会赚上一大笔钱。”他也确实赚到了。与塔列朗不同的是,汉密尔顿对权力的渴望中仍然包含着强烈的共和主义者的美德。[30]
塔列朗还回忆起汉密尔顿思想中的另一个主宰性要素,即“对美国经济前途的坚定信心”。汉密尔顿坚信“旧世界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伟大的市场,肯定也会在美洲建立起来——而且那一天可能不会很遥远”。[31]遗憾的是,作为美国权力的构建者,汉密尔顿没能活着看到那一天。
汉密尔顿在经济国策方面的遗产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有一种罕见的能力,那就是理解权力的体系。作为一名战略家,他能把长远的眼光和实践步骤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美国朝着他所设想的长期目标前进。
汉密尔顿建立的体系以经济和金融实力为基础。他认为国家信用非常重要——不仅是对美国,对其敌人英国也是如此,因为英国也在那场消耗战中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汉密尔顿建立了一套包括流动资本、机构乃至市场心理的体系,让美国的美元和金融市场从此走上了向全球霸主地位迈进的道路。美国直到今天仍在享受这种地位所带来的好处。汉密尔顿还知道,美国的贸易自由和海事关系是这个国家经济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对内对外都是如此。由于汉密尔顿的设想取得了巨大成功,后世的许多美国人经常把他的成就当作理所当然。他们这么想的时候,美国权力的终极来源(经济和金融)就危险了。
汉密尔顿的体系还包括联邦宪法、有效的国家政府,以及常备的海军和陆军。他知道,国家安全和国际影响力靠的是经济、财政、军事实力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作用。他甚至还认识到了技术和创新是如何促进经济和军事实力提升的。
这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把他的系统性观察和地缘政治分析结合在了一起。他知道,美国需要制定一个经济战略和一个安全战略,以在大西洋世界中生存,并控制密西西比河流域。从现实的角度考虑,美国不可能对欧洲列强视而不见,它需要在这些列强之间纵横捭阖,在建国初期积蓄力量的那几十年里尤其如此。汉密尔顿认识到,与英国结成伙伴关系会带来潜在的收益,但是从政治和国家荣誉的需求出发,双方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哪怕英国当时的实力还远强于美国。结果表明,在长达100年的时间内,英国和美国的政界都没有为汉密尔顿所设想的这种关系做好准备。
这位美国国策的构建者误读了或者说没有动员起公众的支持,而且这不是他最后一次犯这个错误。由于美国无法和英国建立伙伴关系,汉密尔顿转向了中立路线。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立一直是美国外交的指南针。不过,中立并不意味着脱离关系。相反,美国所实行的中立政策要求美国的领导人们在运用时采取各种灵活的技巧,以解决他们在各自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将在第7章讲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期间背离了美国的中立政策,但他的具体做法是将“中立”重新定义为一种新型的集体安全。
注释
[1]见G.W.Parke Custis,Recollections and Private Memoirs of Washington(New York:Derby&Jackson,1860),349。Forrest McDonald questions Custis's account in Alexander Hamilton:A Biography(New York:Norton,1982),128.还可见Charles Rappleye,Robert Morris:Financi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Simon&Schuster,2010),454。关于莫里斯的工作,见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Penguin Press,2004),155。关于汉密尔顿成为乔治·华盛顿的助手,见Willard Sterne Randall,Alexander Hamilton:A Life(New York:HarperCollins,2003),122。
[2]Rappleye,Robert Morris,454.
[3]书信原文见“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 Robert Morris,[30 April 1781],”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2,1779-1781,ed.Harold C.Syret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604-635;“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 James Duane,[3 September 1780],” in ibid.,400-418;“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December-March 1779-1780],” in ibid.,236-251。关于汉密尔顿的提议的重要性,见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156;Randall,Alexander Hamilton,231;McDonald,Alexander Hamilton,40。
[4]书信原文见“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 Lieutenant Colonel John Laurens,[12 September 1780],” in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2,426-428。见Randall,Alexander Hamilton,231。
[5]见“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 Robert Morris,[30 April 1781],” in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2,604-635。
[6]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138.
[7]重点看Federalist numbers 11-36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4,January 1787- May 1788,ed.Harold C.Syret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339-490。关于汉密尔顿对《联邦党人文集》的贡献,见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254-255。
[8]McDonald,Alexander Hamilton,156-161.关于皮特父子,见John Lamberton 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Origins of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71。
[9]原文见“Eulogy on Nathanael Greene,[4 July 1789],”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5,June 1788-November 1789,ed.Harold C.Syret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345-359。也可参见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145。
[10]McDonald,Alexander Hamilton,35(粗体强调处为原文所加)。
[11]McDonald,Alexander Hamilton,135.
[12]“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 Robert Morris,[30 April 1781],” in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2,604-635.对汉密尔顿财政规划的分析,见McDonald,Alexander Hamilton,143-210;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291-304;Randall,Alexander Hamilton,373-403;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46-48。
[13]McDonald,Alexander Hamilton,164.
[14]例如,可以参阅托马斯·杰斐逊的文稿编辑,同时也是杰斐逊研究者的朱利安P.博伊德(Julian P.Boyd)的作品:Number 7:Alexander Hamilton's Secret Attempts to Contro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对博伊德的批判性评价,见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74-75;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393-395。
[15]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295.
[16]见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中的总结性章节,尤其是第273、275页。
[17]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393.
[18]汉密尔顿后来与英国首任驻美公使乔治·哈蒙德有过类似的对话,后者于1791年底抵达美国。见“Conversation with George Beckwith,” October 1789,in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5,482-490。见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294-295,394;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49-50,75-82,93-96。
[19]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49,156.
[20]原文见“Remarks on the Treaty of Amity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Lately Mad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9-11 July 1795],”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18,January 1795-July 1795,ed.Harold C.Syret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404-454。见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392,460,461;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158。
[21]关于“偏向英国的和平”,见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273。关于“过去与法国签订的条约所围成的‘囚笼’”,见ibid.,104。关于避免与所有国家产生除商业关系以外的联系,见ibid.,84。原文见“Enclosure:Answers to Questions Propos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15 September 1790],”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7,September 1790-January 1791,ed.Harold C.Syret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37-57。
[22]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169.关于充满激情的实用主义,见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442。
[23]关于建立一支陆军,见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231-237;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556-557。关于汉密尔顿对西班牙的应对计划,见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566-568。
[24]为了避免后代忘记华盛顿的智慧,国会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都会在华盛顿的生日当天朗读这篇演讲稿。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505-509.也可参见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177。关于演讲的起源和影响,见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25]见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83,165。关于起源,见“The Defence No.V [5 August 1795],”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19,July 1795-December 1795,ed.Harold C.Syret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88-97。
[26]书信原文见“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 Oliver Wolcott,Junior,6 June [1797],”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21,April 1797-July 1798,ed.Harold C.Syret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98-101;“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 William Loughton Smith,5 April 1797,” in ibid.,20-21。见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546-547。
[27]见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79,181。原文见“To George Washington from Alexander Hamilton,15-22 July 1790,” in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vol.6,1 July 1790-30 November 1790,ed.Mark A.Mastromarino(Charlottesville,VA: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6),78-83;“From Alexander Hamilton to George Washington [5 November 1796],”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20,January 1796-March 1797,ed.Harold C.Syret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374-375。关于“坦率、善意和有良好的判断力”,见McDonald,Alexander Hamilton,269。
[28]James Thomas Flexner,The Young Hamilton:A Biography(Boston:Little,Brown,1978),449.
[29]Harper,American Machiavelli,56.
[30]关于汉密尔顿和塔列朗,见Allan McLane Hamilton and Willard Sterne Randall,The Intimate Life of 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Skyhorse Publishing,2016),75,195;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465-466,548-549。
[31]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Memoirs of the Prince de Talleyrand,vol.1,ed.Duc de Broglie,trans.Raphael Ledos de Beaufort(London:Griffith Farran Okeden and Welsh,189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