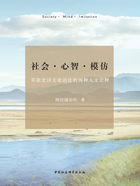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概况和思路框架
第一节 国内外经验、研究概况
一 国内外学术个案和思想体系研究现状
在国外,口传文化学或民俗学的书写模式以事实·思想或理论史为内容,集中于某一学派或某一批重要人物的理论化考察,即重点在于对具体个案及其历史关联的实践化或理论化分析上,而不在于深陷其传记和野史等风趣之泥潭的一般性描述或罗列上。比如,《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1]、《柳田国男描绘的日本——民俗学与社会构想》[2]、《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3]等不仅在深入挖掘其某一学理性侧面上获得成功,还达到了借此投射出整体学科关联性的宏通思考之目的。在此,民俗学界还应该关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的学术史制作经验,而这种从观念、流派和传记的传统模式到以关键的词或概念和问题为导向的相关探索,很好地体现在《文化人类学史序说》[4]、《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5]、《人类学的四大传统》[6]、《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7]和《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8]等中。同理,这种写作模式之转型也反映在民俗学界再熟悉不过的文艺学和美学等领域中,其《近代美学史评述》[9]《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10]、《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11]和《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12]等无疑皆是这样的例子。由此看来,上述写作模式均以关键词、概念、观念或思潮为基点,对其学科实践的历史进行描述或剖析也不乏其特色,但大部分都倾向于辞典式的或教材式的写作模式而忽略了学科理论史的时间深度和内在关联性。另外,从《文学理论》[13]、《文学理论引论》[14]、《批评的概念》[15]、《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16]到《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17]和《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等也意味着书写转型的种种尝试,其中乔纳森·卡勒(J.Culler)批评那些常常给被书写的对象冠以“主义”“学派”“思潮”“理论”和“活动”的名称模式,而安德鲁·本尼特(A.Bennett)、尼古拉·罗伊尔则强调了介于关键词、概念、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袂直径——试图“强化文学理论的实践功能,作者在讨论问题时候并不是采用乏味的概念演绎”,而“是处处利用文学的范例性分析来展示文学创作异彩纷呈的面貌”[18]。在西方的文学史和理论著述中,学术理论史书写作为英美欧学者的发明和独创形式被发展了出来,已基本形成了本质主义、流派理论和核心范畴、问题等不同表达视角之模式;多数以被冠以“主义”“学派”“思潮”“理论”和“活动”等名称的书写模型为基调,陷入了其基于先决理论条件的预设倾向和教材模式的实践困境。
在国内口传文化研究领域,蒙古语口传民俗学的真正学术思想个案研究尚未出现,或者至少并没形成学术史和理论的系统研究,只散见于一些非专题型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文学史、文学研究史和蒙古学历史等实践当中。在前沿工作的翻译方面,有涅克留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19]等。这些均以时间的框架为基本模型,对其主要的学术实践(活动)进行宏通研究,而忽视了一些微观视角的剖析和阐释维度。与蒙古语口传民俗学的学术史研究相比,中国汉语民俗研究学术史探索处于比较全面而相对领先的行列,无论是从理论的探索层面还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说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些著作和译著各有侧重,基于学术思想史和经典个案的以《到民间去——1918~1937 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20]、《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21]、《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22]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等[23]为实践方向,侧重于文艺史和单一文类模式的以《中国神话史》[24]、《中国民间文学史》[25]、《中国民间故事史》[26]、《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27]和《中国神话学》[28]等为具体内容,而注重于学派理论模式的则以《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29]等为实践案例。
作为一种“简明的知识库”,“概念”是表达观念和描述理论的基本工具,同时又是“阐释”维度的集合。这个“阐释”展示“如何以多样化的方式去理解本学科的关键概念和这些方式所经历的变迁,以及未来可预期的变化”[30]。从关系的角度看,这些关键词、概念、观念和思潮等术语却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内在联袂或同一性,它们均体现为某些观念、思想方面的术语化表征和内涵。即,在概念史或观念史的名义之下,揭示在概念或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变迁和不连续性”。该方法本身预示着一种学科历史的“晴雨表”之意味,“同时也正是这些变化所赖以形成的工具”,因而,学术理论史的另一个特点应为“既是回顾总结性的,也是问题式的”。[31]
“概念”是构建的话语及其力量,又是用来表达某一时代的、某一些学者的观点或观念之术语体系;其有可能散见于那些孤立的、零碎的观点或观念表述中,也有可能出现于学术史实践的术语提炼与理论构建中。正如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等所言:
一方面,这些概念可被视为一个个具有某种特定内容与公认价值的金块式信息(information);另一方面,它们又可被当做可能具有的种种意义(meaning)。[32]
在被提升为“概念”之前,概念本身有可能“没有什么内在的、固有的意义”,通过“建构的意义关联”得以或形成“术语化的形式和表述”,而且概念最终“都有不止一层意义”。[33]因而,犹如“战略高地和制高点”的关键概念不是死板的定义,也不是永恒的规范,而是“问题的框架”。这正是任何一位学者都对概念未宣称“自己享有特权接近每个概念的真正意义”之原因所在。[34]在此,“概念”不再指辞典或教材书意义上的规范化术语或名称,而指包含更具广泛内在性的观念、理论、问题、批评、阐释及历史维度等术语化表述。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有关口传文化的民俗学概念借鉴了《民俗学手册》[35]和《美国民俗学》[36]等中提出的“口头民俗”这一术语,与此相同,《民俗学概论》[37]中也引用其上述分类的表达方式同时,还采用了多尔森(R.M.Dorson)等“口头民俗”之说法。
二 中国汉语口传文化研究现状
继1918年左右开端之后[38],中国现代口头传统或口传文化的系统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逐渐进入稳步发展时期,九十年代即20世纪末期已经步入了相对成熟发展时期,到了21世纪更加成熟并取得了全面系统的可喜成就。
汉语神话(myth)和传说(legend)研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西式神话学传入中国以来,以其人类学神话派研究影响最大,这体现在茅盾、黄石、玄朱、谢六逸等对中国神话的相关探索上。[39]与此不同,顾颉刚、袁珂等古史研究者侧重于中国神话或传说的文献传统,并对其进行了具有结合考古学和文献学等色彩的文明复原工作。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后,在20世纪上半叶的神话初探工作基础上,中国现代神话研究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母题方法、历史文献学的考据方法、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心理进化一致说和结构主义方法等,形成了中国式本土化研究的范式特色。进入21世纪初期阶段后,那些传统研究视角已不能满足当前学科发展的需求,但学界也并没有找到更为新的或前沿的理论和方法来完全代替已经形成的以往工作范式。这反映在《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40]、《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41]和《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42]等21世纪初期的相关研究中。正如《民间文学引论》所言,依照袁珂、鲁迅和胡适等对中国神话的相关看法,神话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育。例如,记载“中国早期神话的文献主要有《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等”,但在“占正宗地位的文献《诗》、《书》、《礼》、《易》、《乐》、《春秋》等”中,几乎“寻觅不到神话的踪影”。[43]当然,最值得一提的理论成就是《美术、神话与祭祀》[44]有关神话—仪式的政治权力及其构成学说。在汉语传说研究方面,除了《中国识宝传说研究》[45]和《尧舜传说研究》[46]等中后期探索之外,较为晚近推出的新成果有《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47]等。
汉语史诗(epic)研究。有考察表明,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算起,除了传教士和中国学人对欧洲《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进行介绍和初步研究之外,汉语史诗的早期讨论应追溯到王国维、鲁迅和胡适等开发并挖掘出来的零星关注和相关探究。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史诗研究来说,多数是指有关少数民史诗尤其是蒙古族、藏族和柯尔克孜族等史诗传统的文献研究和田野理论等实践内容。由于各民族史诗研究的各个阶段在工作理念乃至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路径都是相同的,所以下面基于蒙古族史诗研究的整体经验而进行讨论。在蒙古族的民间传统中,史诗事实上是介乎神话和传说等的文类概念,属于结合诗性叙说和展演形式的大型动态民俗事项。比如,仁钦道尔吉、降边嘉措、郎樱、杨恩洪、贾木查和巴·布林贝赫等老一辈知名学者,以及朝戈金、斯钦巴图、诺布旺丹、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等后期成名的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史诗研究,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其中,本书所讨论的《〈江格尔〉论》《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古文)等正是形成于20世纪末期的代表性论著。
汉语民间故事(folk story 或 folk-tale)研究。这项工作也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探索和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已经进入了较为稳定发展的成熟阶段。民间故事研究是一个术语体系完整、研究团队较庞大的民间文艺学分支领域。除了厚重悠久的文献记述、大量现场记录的文本积累等之外,其取得的成就还与在历史—地理学派的类型学方法、流传学派理论、文化人类学方法、结构—形态学、展演理论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术工作分不开。譬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英文版1978)等早中期阶段成果不仅对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体系的初步搭建起到决定性作用,还对后期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中后期工作则以陆续出版更为全面系统的专题论著为特色,主要有《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48]、《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49]、《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50]、《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上中下卷)[51]、《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52],等等。
汉语民间歌谣(folk song)和祝赞词(eulogies)、禁忌语(taboo terms)研究。其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恢复重建工作,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发展态势。在这些相互关联的专题研究方面,有《〈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53]、《禁忌与中国文化》[54]、《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55]、《中国禁忌史》[56]、《岁时记与岁时观念》[57],等等。
三 中国蒙古语口传文化研究现状
蒙古神话和传说研究。在蒙古学界,早期学者对神话(myth)和传说(legend)的理解较为模糊,并把两者合在一起统称tomog yariya或uliger。后期学者为了区分tomog和olamjilal yariya的不同含义,称神话为tomog或siditu uliger;称传说为tomog或olamjilal yariya。在20世纪60年代,蒙古神话、传说研究以零星发表的少量论文为起点,其不仅作为蒙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序幕或开端,而且以“文献—考证”为主的研究模式却成为其全部立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批学者沿着“文献—考证”这一路径方向迈出了更大的一步,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文学理论等的结合视角对《蒙古秘史》中的“阿伦高娃母亲传说”(1981)、“阿阑豁阿传说”(1983、1984)、“都蛙·锁豁儿传说”(1990、1991)、“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神话传说”(1990)进行考察,讨论了文化人物神话的来源、与独目巨人神话的比较,以及蒙古族创世神话和萨满教九十九天说之间的关系(1989)等话题。这些探索无疑为以后的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丰富了其方法论和视角。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期,蒙古神话传说的研究已进入较成熟发展阶段,这无不与《蒙古族神话选》[58]、《蒙古神话形象》[59]、《蒙古神话新探》[60]、《蒙古神话传说的文化研究》[61]、《蒙古神话比较研究》[62]、《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63]、《蒙古族历史传说》[64]、《成吉思汗的传说》[65]、《蒙古传说大系》[66]、《布里亚特传说渊源》[67]等成果的相继出版有关。这些著述的旨趣集中在神话传说的概念界定、艺术特征及内容思想探讨或某个单一神话传说的解读和比较研究上。这项工作不仅为蒙古神话和传说研究提供新的视域空间,还将其推进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一书,把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分为开天辟地神话、熊和犬图腾崇拜神话、狼图腾神话、日月星辰神话、腾格里信仰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洪水神话、物种起源神话、动植物神话、盗火神话与文化英雄神话等类型,并对其进行了基于文献—实证分析方法的文学比较研究和民俗学母题研究等系统考察。
蒙古史诗研究。该论域开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关于研究学习民间诗歌之管见》(1954)可谓早期对韵文文类进行探究的开创性文章,随后一大批蒙古学者也参与进来一道开启了史诗文类研究的整体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英雄史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纵观蒙古史诗研究的发展历程,可将它分为四个阶段:传统的文学历史学研究、母题类型学研究、古典美学的诗学研究和口头诗学研究等。
第一,传统文学历史学的研究,把脱离语境的史诗文类视作纯文学作品来看待,对其史诗文类的题材、内容、主题及艺术特征等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性研究,甚至仅仅停留于作品的介绍或相关界定等方面。
第二,母题类型学研究,这是深受俄苏学者及德国学者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探索趋势,也是传统文学历史学研究的延续和发展。对于此类探索而言,问题的核心在于史诗文类的地理分布、母题类型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原型脉络等方面。宝音贺嘉格等有关母题和类型研究的文章不仅标志着母题理论的正式引进,而且激发了一批青年学者决定置身于史诗研究的热情。随着对这一演进趋势的热烈讨论,蒙古史诗研究一方面迈出了把目光投向于国际化的新步伐,另一方面还酝酿出了一批大量的学术专著。其中,仁钦道尔吉先生多年潜心研究蒙古英雄史诗,对我国史诗研究乃至国际史诗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史诗研究力作《〈江格尔〉论》和《源流》[68]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源流》中,作者结合自己的田野经验和国外理论的新颖视角,对蒙古史诗的产生年代、地理分布与分类、宗教文化内涵等进行了系统研究。之后,《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69]、《蒙古史诗生成论》[70]、《蒙古文学叙事模式及其文化蕴涵》[71]、《蒙古突厥史诗人生礼仪原型》[72]等均以母题理论的深化发展为探索历程,丰富了其研究视角多样化的可能性路径。
第三,古典式美学的诗学研究,即蒙古史诗的诗学考究,其历来就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种难点问题。比如,巴·布林贝赫先生结合多年的丰富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对蒙古史诗进行美学意义上的解读和探究,开辟了新的诗学领地,提升了史诗研究的高度。《蒙古诗歌美学发展轨迹》(1987)、《〈江格尔〉中的自然》(1989)、《英雄主义诗歌——英雄史诗》(1989、1990)到《蒙古英雄史诗中马文化及马形象的整一性》(1992)、《英雄史诗的宇宙结构模式》(1996)、《〈江格尔〉的英雄主义》(1997)、《〈江格尔〉中的宇宙模式》(1998)等标志着蒙古史诗诗学研究的整体化考察历程;这不仅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的广泛兴趣,还引领其带入了追求史诗诗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中,《史诗的诗学》[73]是一部20世纪最后阶段诞生的古典美学式史诗诗论研究之典范,也是逐渐被学界认同为影响力非凡的探索高峰的一部力作。该书共有八章,对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特征、宇宙模式、形象体系、文化内涵及意象诗律风格等进行了美学意义上的诗学探究,总结出了理论上的规律和特征。尤其是史诗形象诗论为蒙古口头文类的形象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视角,又大大推动了口头传统研究形象学方面的更广泛的探索进程。之后,深受上述影响的有《蒙古民间文学艺术形象研究》[74]和《蒙古民间文学基本体裁与马形象文化学研究》[75],等等。第四,口头诗学研究是在2000年左右出现的一种新突破,也是在中国史诗尤其是蒙古史诗研究领域获得的重大进展。例如,《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简称《口传史诗诗学》)一书[76]的诞生就是这一进展的有力见证,该书以冉皮勒演唱的史诗片段为分析对象,与以往蒙古史诗研究进行激烈对话,还探析了史诗文本类型、传统与语境、史诗文类的程式与句法等论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新疆江格尔齐研究》[77]、《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78]等。这一学术理念,不论从方法论意义上还是从口头文本观的根本性改变上来说,无疑对国内口头传统研究乃至整个民俗学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与上述蒙古史诗研究相比,蒙古族说唱艺术的研究也大约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与蒙古族现当代说书艺人毛依罕(1950)、琶杰(1955)等的演唱活动也有着紧密联系。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蒙古族说书故事研究进入了展开搜集、整理、介绍和探究的全面开花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论文数量达到了数百篇以上的规模,还问世了积累和进步可观的一些学术专著。到了21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一批较为成熟的专题论著,有《胡仁·乌力格尔研究》[79]、《琶杰研究》[80]、《毛依罕研究》[81]、《说书艺人与胡仁·乌力格尔、好乐宝、叙事民歌》[82]、《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83],等等。就国外研究而言,1970年左右匈牙利学者卡拉(G.Kara)在有关蒙古民间艺人的诗歌研究中,专门讨论了琶杰演唱的好乐宝和《格斯尔》的部分内容。苏俄汉学家李福清(B.Riftin)也聚焦于本子故事与口头文学的比较视角,对书面与口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究,为蒙古说唱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1979年,德国学者海西希(W.Heissig)出版《蒙古英雄史诗卷》(第八卷),对蒙古说书进行了系统研究;海西希和策仁索德纳姆曾合作并编写过本子故事演唱篇目,后来策仁索德纳姆还整理出版了毛依罕演唱的《胡日东巴特尔》。除此之外,波佩、涅克留多夫等也为胡仁·乌力格尔研究倾注了心血,做出了贡献。
蒙古民间故事研究。它开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左右,研究焦点仍徘徊在民间机智人物的故事探究上。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代表着当时的研究旨趣和水准,从对故事文类的介绍、界定,或对艺术特征及思想内容等进行系统分类和类型学剖析也可见一斑。此外,有一部分学者对民间故事的情节结构等进行了探究,另一部分学者却对尸语故事的跨文化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自20世纪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期是蒙古民间故事进入系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批有关民间故事研究的专题论著。《蒙古民间故事研究》[84]首次填补这一历史空白,改变了缺乏系统化研究的零散现状。该书对民间故事文类的特征、类型进行界定、归类,把它分为童话、生活故事、寓言故事、幽默故事、文人故事五个类型,深入探讨了五大类型民间故事的相同点和变异特性。《蒙古民间魔法故事类型研究》[85]是对单一类型蒙古民间故事展开类型学研究的成功案例,开拓了专题类型研究的新论域。该书基于母题、类型研究法和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蒙古民间魔法(神奇)故事进行了类型学意义上的解读。即,通过对大量故事文本的分析,勾勒出蒙古民间魔法(神奇)故事的15个类型:《天鹅仙女》《青蛙儿子》《龙女》《金胸银臀儿子》《灰姑娘》《兄弟俩》《金银阿日盖》《阿仁珠拉》《羊尾巴儿子》等。由于受其历史—地理学派和文化人类学进化论等方法论影响,作者力求揭示故事母题的原型、传播、变异特征及原始文化内涵(信仰、仪式、习俗)等。后来,沿着这一方向,更多学者也投身于单一类型故事的类型学研究或比较研究而纷至沓来,拓宽了这类研究的视域,丰富了研究成果。例如,《蒙古民间故事类型学导论》[86]和《蒙古族古今文学精粹——民间故事卷》[87]等的工作原则均倾向于上述历史—地理学派的母题类型研究范畴。
蒙古民间歌谣和祝赞词、咒语研究。民间歌谣类研究也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研究主要对蒙古民歌尤其是布里亚特等单一族类民歌的渊源、类型、作品思想及艺术特点等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性和描述性探究。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该分支领域立足于文学理论的本位视角,对《嘎达梅林》《森吉德玛》《陶克陶胡》等民歌的各种艺术特征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自九十年代至今,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的系统化,陆续问世了一些民歌研究的著作和学位论文。比如,《蒙古族音乐史》[88]《卫拉特民俗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研究》[89]等从不同角度对蒙古民歌做了较为全面的体系化考察。另外,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蒙古口头韵文——祝赞词、咒语研究,最初的探索几乎都集中在于韵文文类的介绍、简单论析等的描述性探究。这样例子有:《论谜语》(1960)、《谈蒙古族谚语》(1963),等等。随着学术队伍逐渐庞大,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对其各种韵文文类的界定、分类、作品思想、艺术特征及发展脉络等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性研究。迈入20世纪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期之后,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已出现了不少的学术专著和学位论文,其标志着这一专题研究方向的壮大和系统化发展。例如,《蒙古族祝颂词的多层次文化内涵》[90]作为一部填补蒙古韵文专题研究历史空白的专著,从象征学的角度出发,对其祝赞词所蕴含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详尽的探究。
四 仁钦道尔吉和巴·布林贝赫的专题研究现状
仁钦道尔吉和巴·布林贝赫两位老一辈学者皆是我国蒙古学领域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民间文艺学家,可谓卓尔不群的学术引领者。他们的研究视角独特,见解独到,内容广泛,几乎涵盖了文艺理论、民间文艺理论以及美学和文化学等领域的方方面面。理论构建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的独创性研究是两位学者始终追求的学术理念,也是他们共同的立论基石。《〈江格尔〉论》[91]、《源流》[92]和《论纲》[93]、《史诗的诗学》[94]作为两位史诗学者的主要代表作,在那些同时代史诗研究成果里巍巍矗立,虽说屈指可数,但厚重如山。这些学术论著不仅代表着20世纪国内蒙古史诗学的领先水平,还奠定了他们各自在蒙古学,尤其是国内史诗学领域里的中坚地位。因而,民间文艺学或诗学的规律和法则、叙事类型的结构问题一直都是他们共同关心的核心课题,也是其为此作出理论贡献的起点和归宿点。
在国内,蒙古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理论的个案问题算是一片未开垦的新领域,尤其蒙古史诗学的个案分析研究应亟须得到突破性的进展和探索。目前,有关草原史诗学个案的散论性文章多以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形式集中在蒙古文学史、蒙古文学学术史、蒙古学学术史等方面,基本属于非专题型的描述性研究,而不属于以学术理论的历史化语境为背景或前提的真正意义上的分析研究。就学术史个案和理论分析的结合性尝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至今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关注和重视。所以,以往蒙古史诗学历史方面的一般性梳理主要还是介绍性的或非专题性的描述性研究,而不是以系统的或专题的学术个案为切入点的、将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专题研究。比如,关于类型学问题的介绍性评论有:《〈江格尔〉研究的一部佳作——简论仁钦道尔吉教授〈江格尔〉论一书》[95]、《中国史诗研究正走向世界——中国史诗研究丛书首发式暨学术座谈会综述》[96]、《〈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一书出版》[97]、《蒙古英雄史诗资料建设的里程碑——关于〈蒙古英雄史诗大系〉》[98]、《我的学术研究道路》[99],等等。关于诗学问题方面的评论性文章有:《巴·布林贝赫诗论的美学思想》[100]、《巴·布林贝赫史诗诗学的研究方法》[101]、《畅游诗海的人——记著名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教授》[102]、《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及他的诗学理论》[103]、《巴·布林贝赫诗学研究》[104],等等。由是观之,以上文章以散论性和介绍性的描述研究为中心,并没有把诗学和类型学问题还原于蒙古史诗学的历史语境而进行系统化的个案分析和理论归纳。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尝试性的介绍和评论为诗学和类型学问题的深入探究提供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学术信息和材料来源。
在国外,对具体史诗文类的分析性研究较多,而对研究著述的概括性和分析性研究相对少。例如,除《英雄史诗的起源》[105]外,涅克留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可谓这方面的唯一特例,该书(尤其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疏理了蒙古史诗研究在欧美地区的理论化构建及观念史问题,并以弗拉基米尔佐夫、扎木查诺、桑杰耶夫、波佩、鲍顿、萨嘉斯特和劳仁兹等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为考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