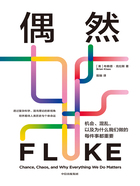
第1章
引言
如果你的人生可以倒带回到最初,重新按下播放键之后,一切还会和原来一样吗?
1926年10月30日,史汀生夫妇来到日本京都。他们下了蒸汽火车,住进宫古岛酒店56号房间。[1]安顿好后,他们漫步于日本昔日帝都,感受着城市中秋日的缤纷色彩——枫叶已变成了深红色,银杏树绽放出金黄色的光芒,峥嵘繁茂的树木高高耸立在郁郁葱葱的青苔之上。史汀生夫妇参观了京都的传统日式庭院,这些庭院掩映于城市泥岩山丘之中。他们为一座座历史悠久的寺庙而惊叹,寺庙中每一根木头似乎都凝刻着昔日幕府时代的荣光。六天后,史汀生夫妇收拾行李,结账离开。
然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宫古岛酒店账簿上史汀生的名字将被写入历史,成为之后一系列事件的起始。在那些事件中,一个人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在一念之间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但不幸的是,他也给其他地方的十几万无辜者带去了死亡。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私人观光旅行。
19年后,在离京都一万多千米的美国新墨西哥州,一群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和军队将领聚集在一个代号为“Y站”的绝密地点。那是1945年5月10日,纳粹德国投降后第三天。此刻,太平洋上还在上演着一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血腥消耗战。然而,在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偏远哨站,科学家和军人们看到了终结战争的希望——一种新型的、具有无法比拟的破坏力的武器,他们称之为“小玩意”。
虽然此时还没有任何一场成功测试能展示出这种新型武器的全部潜能,但Y站的每个人都感觉离成功越来越近了。为了早日做好准备,项目组成立了一个13人的“目标委员会”,这些精英人士将决定如何让全世界见识到“小玩意”的威力。该用它摧毁哪个城市?他们一致认为东京并不合适,因为之前猛烈的大轰炸已经摧毁了日本的这座新首都。经过权衡,他们商定了一个目标——将第一枚炸弹投向京都。[2]
京都是战时日本新工厂的聚集地,其中一家工厂每月可生产400台飞机发动机。[3]此外,从战略上看,将曾经的首都夷为平地,想必能给日军士气造成毁灭性打击。目标委员会还注意到一个无关紧要但可能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京都是日本的知识中心,教育人口众多,著名的京都大学就坐落于此。委员会认为,京都的幸存者会认识到,这种新武器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日本不仅输掉了战争,在科学的战场上他们输得更彻底。于是目标委员会一致认为:必须摧毁京都。
委员会还商定了三个备选目标:广岛、横滨和小仓,并将该目标清单呈送杜鲁门总统。接下来,他们需要做的就只是等待原子弹就绪了。
1945年7月16日,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广袤的空地上成功试爆,核能时代破晓而出。目标委员会的任务终于不再只是开展理论分析工作了。军事战略家们查阅了京都的详细地图,并决定将爆炸地点定在京都的铁路调车场。[4]这里距史汀生夫妇20年前住过的宫古岛酒店大约只有800米。
1945年8月6日,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从天而降,但它没有落在京都,而是被“艾诺拉·盖”号轰炸机投到了广岛。近14万人因此而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三天后,也就是8月9日,“博克斯卡”号轰炸机在长崎投下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又导致约8万人丧生。
为什么京都能够幸免于难?为什么长崎这个未被列入头号轰炸目标的城市会被摧毁?值得一提的是,大约20万人在生死线上经历了摇摆,而起因只是一对游客夫妇和一片云层。
1945年,亨利·L.史汀生先生已成为美国战争部长,他是美国负责监督战时行动的最高文职官员。作为非军队人员,史汀生认为他的工作是制定战略目标,而不是具体指引将军们如何完美实现这些目标。但是,当目标委员会选择摧毁京都时,这一切都改变了。
史汀生立即行动起来。在一次与曼哈顿计划[5]负责人的会议上,史汀生强硬地摆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不同意轰炸京都。”[6]在与美国军方的讨论中,史汀生重申:“没有我的允许,他们绝不能轰炸京都。”[7]然而,尽管他一再坚持,京都还是持续出现在轰炸目标名单上。将军们执意认为京都符合所有条件,应该炸平它。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史汀生要如此固执地一心保护这个日本战争机器的神经中枢。
将军们当然不知道宫古岛酒店,不知道雄伟的日本枫树,也不知道金色的银杏树。
史汀生坚定不移地在高层游走。1945年7月下旬,他两次会见杜鲁门总统,[8]每次都表示坚决反对摧毁京都。杜鲁门终于松口了,将京都排除在考虑范围外。最终目标名单包括四个城市:广岛、小仓、新潟,以及后来加上的长崎。史汀生拯救了这座被将军们戏称为史汀生“宠儿城”[9]的古老城市,第一颗原子弹改为投放在广岛。
第二枚炸弹原本计划投向小仓,但当B–29轰炸机接近小仓时,云层遮挡了视线,[10]飞行员难以看清下方目标。陆军气象学家小组曾预测小仓当天天空晴朗,而云层的出现纯属意外。飞行员驾驶着轰炸机在空中盘旋,希望云层能散开,但一直没等到理想的能见度。最后,机组人员决定不冒空投失败的风险,而是转向攻击次要目标。他们接近长崎时,发现这座城市也被云层遮住了。在燃料快耗尽时,他们尝试了最后一次飞行。云层在最后一刻散开了。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02分,原子弹“胖子”落下。长崎的平民何其不幸:这个城市在最后一刻才被列入目标名单,它被夷为平地的原因只是另一个城市上空飘过的云层。如果轰炸机早几分钟或晚几分钟起飞,小仓的无数居民可能成为原子弹下的亡魂。时至今日,每当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逃过一劫时,日本人都会说这是“小仓的运气”[11]。
* * *
云层使一座城市幸免于难,而一对夫妇几十年前的度假之旅拯救了另一座城市。京都和小仓的故事对我们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直接挑战,我们倾向于以一种简化、便捷、有序的方式看待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能够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可以用理性来解释混乱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成千上万人的生死不应该取决于十几年前一对夫妇愉快的旅行回忆,也不应该取决于天空中恰逢其时飘过的云。
小孩子总是不停地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知道简单的因果模式——由X到Y。这很有用,它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化版的现实——一个原因引起一个结果。通过因果思维,我们可以从事件中提炼出自己能理解的清晰关系,进而驾驭复杂的世界。触摸热炉子会导致疼痛,吸烟会引发癌症,云会带来雨水等。
然而,在几十年前的日本,云层带来的直接后果不是雨水,而是一个城市遭遇灭顶之灾,另一个城市幸免于难。更奇特的是,长崎的无妄之祸源自一系列随机因素的组合,这些因素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而且它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环环相扣,才导致广岛和长崎上空的“蘑菇云”,比如:裕仁天皇的崛起、爱因斯坦在19世纪末出生、数百万年前地质变迁的力量锻造出了铀、无数士兵牺牲于太平洋战场、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中途岛战役,等等,直到最后,一次关键的假期和一片关键的云转动了命运的齿轮,如果之前无数因素稍有改变,一切都会不同。
如果我们回望自己的一生,可能会发现自己也曾经历过小仓式的幸运(尽管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当我们思量这些“假设时刻”时,很明显,一些任意、微小的变化和看似随机的意外事件会改变我们的职业道路,重新安排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颠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为了解释我们何以成为如今的自己,我们会承认,在许多人生的转折点上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其转向。然而,我们还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转折点,那些我们不可能意识到的重要时刻,以及那些让我们同生死“擦肩而过”却不自知的时刻。因为我们从未感知,也永远不会预知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既然我们连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无法分辨,又怎能明白哪些因素是事关紧要的呢?
如果数十万人的生死取决于一对夫妇几十年前的度假之旅,那么哪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或事故可能最终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开会迟到或错过高速公路出口除了会影响你的个人生活,还会牵涉历史进程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你能否意识得到?或者,你完全不会觉察到,自己在茫然无知间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们对“当下”和“过去”的看法存在一种奇异的脱节。当我们设想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时,得到的警告都是:确保不要触碰任何东西!因为对过去的微小改变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你甚至可能不小心把自己从未来抹除。但当我们谈论当下事物时,就不会有这种担忧。没人会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走路,以防不小心压死一只虫子;很少有人会因为错过公交车而对不可控的未来感到惶恐不安。相反,我们会认为这些小事并不重要,因为一切影响最终都会被时间冲淡。但是,如果说过去的每一个细节都创造了我们的现在,那么现在的每一刻也正在创造我们的未来。
1941年,原子弹爆炸的四年前,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写了一篇名为《小径分岔的花园》[12]的短篇小说。该故事的核心隐喻是,人类在一个花园中漫步,而脚下能走的路在不断变化。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看到无限可能的世界,但在当下,我们必须决定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我们每迈出新的一步,面前的道路都会发生变化,它会无休止地分岔。每一步都会开辟新的未来,同时阻断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每一步都很重要。
但这个故事中最令人惊叹的启示是:我们的道路并不完全由自己决定。相反,我们所在的花园是由前人开拓而成的。我们面前的道路其实是过去历史的分支,是由别人的脚步所铺就的。而更让人感到茫然失措的是:前方道路的样子不仅取决于你的选择,因为在你移动时,这些园中的小路也会因周围其他人的选择而被频繁重塑。在博尔赫斯为我们描绘的这幅画面中,我们选择的道路常常被无情地调转方向,我们前行的轨迹总是被他人细微的举动所改变,而我们却一无所察,那些隐秘的京都和小仓时刻决定了我们未来将去向何处。
然而,当我们试图解释这个世界,解释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来到这里,以及这个世界为何如此运转时,我们却忽略了“偶然”。被压扁的虫子,错过的公共汽车,所有这些我们都认为毫无意义。我们故意忽略了一个常令人感到手足无措的事实:只要有一些微小改变就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当我们探寻其中直接的因果关系时,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诉诸现实的精简版本。如果X导致了Y,那么X一定是主旋律,而不是一个轻微、随意的小音符。所有事情都可以被预测,可以被绘制为图表,并通过适当干预来加以控制。我们受到权威人士和数据分析师的诱导,这些预言家常常做出错误判断,但很少认为未来无法确知。当我们在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令人欣慰的确定性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往往会选择后者,尽管后者更有可能是错的。或许,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能理解一个由偶然所造就的世界吗?
* * *
1905年6月15日,克拉拉·马格达伦·詹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詹姆斯敦的一个小农舍里杀死了自己的四个孩子:玛丽·克莱尔、弗雷德里克、约翰和西奥多。她清理了他们的尸体,把他们塞进床上的被子里,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丈夫保罗下班回家,发现全家人都躺在小床的被窝里,停止了呼吸。这肯定是人类所能体验的最可怕、最痛苦的经历之一。
哲学中有一个被称为“命运之爱”(amor fati)[13]的概念[14]。我们必须承认,生活是我们之前一切经历的累积的结果。往上数四代,你可能不知道自己那八位祖辈的名字,但当你照镜子时,你看到的是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唇以及其他特征的融合,你的面孔记载了那早已被遗忘的时光。当遇到陌生人时,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事实:他们的直系祖先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有孩子前就去世了。这是废话,但也是事实。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在特定的时间相遇、结合,你就不会存在。即使他们彼此错过,也会遇到其他爱人,生出其他孩子。
往上追溯几千年,你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和曾曾祖父母与你也有同样的关系。你的生命取决于中世纪无数人的求爱,取决于冰河时代你的先祖对抗剑齿虎时的艰难求存,如果再往上追溯,它还取决于600多万年前黑猩猩的择偶偏好。如果把人类的血统追溯到数亿年前,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取决于一种类似蠕虫的生物(谢天谢地,它没有被压扁)。如果这些配偶没有按照已有的历史剧本相爱、生活和生存,如果生物链没有按照自己的剧本严谨运行,现在在读这本书的就可能是其他人,而不是你了。我们是命运链环的突围者,如果过去的某个结点稍有改变,我们就不会待在这里了。
回到威斯康星州的小农舍,那个保罗正是我的曾祖父——保罗·F.克拉斯。我的中间名是保罗,这是他留下的姓氏。我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克拉拉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克拉拉在一个多世纪前,不幸地斩断了自己的血脉分支。保罗后来再婚了,娶了我的曾祖母。
在我20岁时的某一天,我父亲郑重地叫我坐下来,然后递给我一张1905年的新闻剪报,标题是《可怕的疯狂女人》[15],这则新闻揭露了我们家族史中最令人惶恐不安的一章。他还给我看了克拉斯家族在威斯康星州的墓碑的照片——所有孩子的墓在一边,克拉拉的在另一边,他们的死亡日期是同一天。这让我很震惊。但更让我震惊的是,我意识到,如果克拉拉没有自杀,没有谋杀她的孩子,我就不会存在。一桩阴森可怖的血案让我的出生成为可能,而那四个无辜可怜的孩子死了。现在我活着。你在阅读我的作品。命运之爱意味着我们要接受甚至拥抱事实,还要认识到我们是过去种种美好与黑暗的衍生物,前人生活中的胜利与悲剧共同构成了如今我们身在此处的缘由,我们的存在要归功于他们的仁慈与残忍、善良与邪恶、爱慕与仇恨。如果没有发生以往的种种,我们也不会是我们。
“我们都会死去,这让我们成为幸运儿,”理查德·道金斯曾经评论道,“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死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出生。这些本可能占有我们生命,但实际上永远淹没于‘可能’深渊中的人,比阿拉伯大沙漠中的沙粒还多。”[16]这些存在于未来无限可能性中的生命,被道金斯称为“未诞生的幽灵”。他们的数量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只要做出最微小的调整,一个生命就会被另一个生命所代替,后者会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过着不同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存在,好似建立在叠叠高游戏中的木塔之上,岌岌可危,摇摇欲坠。
为什么我们要假装现实并非如此?我们存在的根基确实很脆弱,但这一事实违背了我们根深蒂固的直觉——我们坚信世界的运行规律应该是另一种模式:重大事件的起因理应是重大事件,而不会是微小的偶然事件。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接受的专业训练是:要探寻能引出Y的X。几年前,我去了非洲南部的赞比亚,目的是研究为什么一场政变失败了。是因为原政治体系足够稳定吗?或者,是因为政变缺乏民众支持?我出发去寻找其真正的原因。
赞比亚政变的阴谋很简单,但也很有效:叛军头目派兵绑架了军队指挥官,他们计划逼迫司令官通过无线电宣布政变。策划者的预期计划是:一旦军方高层下达了命令,营房里其他士兵就会加入政变,这样政府就会崩溃。
但我采访了参与绑架的士兵后,感到自己所学的所有现实模式都崩溃了。当叛军闯入军营时,司令官从床上跳起来,跑出后门,爬上围墙。追赶他的叛军士兵伸手抓他裤管,想把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司令官拼命向上爬,而士兵努力想把他从墙上拽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电影中的慢动作画面一样:士兵抓住了司令官的裤管,但裤管从他指尖慢慢滑脱,司令官翻过墙逃跑了。顷刻之间,政变土崩瓦解。如果这个士兵再快一毫秒,或者他手再攥得紧一些,原有政权可能就会垮台。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民主出于“偶然”侥幸存续了下来。
萧伯纳在1922年创作的戏剧《千岁人》中写道:“有些人看到已有的情况,然后问:‘为什么会这样?’我梦想着从未出现的情况,然后问:‘为什么没有这样?’”[17]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每个人的存在都以近乎无限数量的往事为前提,只要它们稍微变动,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世界?在单个人的生命取决于其他人的死亡(像我一样)或者民主靠裤管布料存续下来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社会?当我们思考宇宙的无限可能性时,我们可以想象出不同的世界。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世界可供观察,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对过去做了微小改动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如果史汀生一家在1926年错过了那班去京都的火车,转去大阪度假,结果会怎样?如果前往小仓的轰炸机晚起飞几分钟,赶上云层散开,结果会怎样?如果我的曾祖父在那个悲惨的日子早点回家,结果又会怎样?世界将会不同,但会如何不同?
我是一名(幻想破灭的)社会科学家。幻灭是因为我长久以来总有一种心绪不宁的困扰:我们“假装”世界按某种方式运转,但实际上它并非如此。我对现实的复杂性研究得越多,就越怀疑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令人欣慰的谎言之中,从我们讲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到我们用来解释历史和社会变迁的神话,莫不如是。我开始怀疑,人类是否在参与一场无休无止但徒劳无益的抗争——我们试图将秩序、确定性和理性强加给一个由无序、偶然和混乱主宰的世界。但与此同时,我逐渐倾心于另一个迷人的想法:只要我们接受了自我和周围的一切都源自宇宙偶然的安排,我们也可以在混乱中找到新的意义,并学会乐观面对混乱而不确定的现实。
这种异端观念违背了我从主日学校到研究生院所接受的所有教育。正统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你只需找出这个原因:如果你想了解社会变革,就多读历史书和社会科学论文;如果你想了解人类诞生的故事以及现代人是从哪儿来的,就去深入研究一下生物学,以及达尔文的学说;如果你想探索生命中未知的奥秘,那就多读些哲学巨匠的著作;如果你想了解宇宙的复杂机制,那就学习物理学吧。
但是,如果这些永恒的人类之谜都是同一重大问题的一部分呢?
具体来说,人类必须应对的最大谜题是:为什么事情会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读的书越多就越意识到,当这个巨大谜题摆在眼前时,我们无法从政治学理论、哲学巨著、经济学模型、生物进化论、地质学研究、人类学论文、物理学证明过程、心理学实验或神经科学讲座中摘取现成答案。相反,我开始认识到,人类每个不同的知识领域都为此提供了一个片段,如果把它们结合起来,便能让我们更接近这一难题的答案。本书想要挑战的目标正是试图将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形成一幅连贯的新画面,以重塑我们对“我们是谁”及“我们的世界如何运作”的认知。
当足够多的拼图碎片拼在一起时,一幅崭新的画面就会出现。当我们看到它逐渐清晰的轮廓后,我们就有希望用一些更接近准确真相的想法,来取代那出于心理安慰而自我编织出的谎言,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源头上颠覆我们根深蒂固的世界观。衷心提醒: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觉得这种转变会让人迷失方向。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让人迷失方向的时代了,想想阴谋政治、大流行病、经济震荡、气候变化以及由人工智能创造的可扭曲社会的新型“魔法”。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们中许多人早就在一片不确定的海洋中感到迷茫无助了。当我们在茫茫大海中不知所措时,还紧抱着自我安慰的谎言,这只会让我们沉入海底。而此时,最好的救生筏可能就是真相。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简洁有序的叙事要让位于由偶然、混乱和随意性所交织而成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中,无论多么微小的时刻,都可能至关重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揭开一些我们自己写就的谬见,它们的破坏性更甚于简单的因果思维,却常常被人们奉为圭臬。另外,为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我还会探讨三个关于人类的重要问题:第一,我们何以成为如今的人类,以及为什么这对我们很重要;第二,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被无法掌控的意外和随机事件无休止地改变的;第三,为什么我们会经常误解现代社会的动态关系。即使是最小的“偶然”也会造成影响,诚如已故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最有限的情况下,最微小的行动都会孕育出无限的可能,因为一个行动,有时是一句话,足以逆转星辰。”[18]
* * *
有些读者可能已经开始反对这些大胆狂妄的说法了。如果故事书中所说的现实不是真的,偶然和随机所引发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要多,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历史和宇宙中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秩序?的确,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稳定的,世界充斥着规律和令人欣慰的常规模式。也许是我言过其实了,除了如京都那类寥寥可数的奇怪事件,生活中的大多数随机遭遇和偶发事件都无关紧要。真是这样吗?
几十年来,进化生物学领域被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割裂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主张生命进化会按照某个既定轨迹稳步前行;另一个阵营则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生命之树会永远开枝散叶,并被偶然和无序所左右。生物学家用一组对立的术语点出了这一争辩的关键:世界是发散的还是趋同的?问题的核心在于,进化是否能以可预测的方式进行,而不考虑反常事件和随机波动,或者说这些偶然性是否会导致进化走上歧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术语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达尔文理论,认识加拉帕戈斯群岛雀鸟的喙,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在的社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折。
设想我们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你可以倒退回昨天。在新的一天开始时,改变一个小细节,比如你在冲出门之前停下来喝杯咖啡。如果无论你是否停下来喝这杯咖啡,你这一天过得都差不太多,那么这就是一个趋同事件。该发生的事无论如何注定要发生,你生命的火车只是晚几分钟离开车站,但还是沿着同样的轨道行驶。然而,如果你停下来喝了咖啡后,你未来生活的一切都以不同的方式展开,那么这就是一个发散事件,因为很多事情都会因为这一件小事而发生改变。
自然界似乎在发散性和趋同性之间摇摆不定。6 6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4千米的小行星在地球坠落,它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100亿枚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这颗小行星撞击了尤卡坦半岛浅海下富含石膏的岩石,巨量的有毒硫黄释放到大气中,同时还有无数的岩石粉末被抛入大气层,产生了强烈摩擦,最终形成“红外脉冲”[19]。这次撞击致使地球表面温度骤然升高了260摄氏度,恐龙就像烤箱中的烤鸡。[20]
遭遇小行星撞击后,地表被严重炙烤。幸存者大多分为两类:一类可以钻入地下,另一类生活在海洋中。我们观察如今尚存的动物,从丛林生物到沙漠生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小行星撞击事件后幸存者的进化分支,都源自当年一种足智多谋的掘地求生的动物。[21]
只要改变一个细节,我们就能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小行星早一瞬或晚一瞬撞击地球,它就会坠入深海而不是浅海,这样一来,其释放的有毒气体就会大量减少,灭绝的物种也会大幅减少。如果小行星的撞击时间推迟一分钟,它可能会完全错过地球。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提出,这颗小行星来自太阳穿过暗物质时所产生的振荡。[22]她认为,这些微小的引力扰动将小行星从遥远的奥尔特云抛向了地球。如果不是在遥不可测的太空深处发生了一次微小振动,恐龙可能会幸存下来,而人类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这就是发散性。
现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网膜进化出了极为复杂且具有专用功能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这些细胞使我们能够感知光线。我们的大脑再对感知到的光线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将其转化为生动的图像呈现。这些能力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但在地球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生物都是没有眼睛的。直到一个随机突变意外地产生了一组感光细胞,具备这类细胞的幸运儿可以分辨出自身处于明亮还是黑暗的环境中,这有助于它们生存。随着时间推移,感光的生存优势通过自然选择得以强化,最终使我们拥有了复杂的眼睛,这源于一段被称为“PAX6基因”[23]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片段的突变。乍一看,PAX6基因突变似乎是一个发散事件:祖先幸运地走上了一条分岔路,导致数百万年后的我们可以欣赏精彩的剧集。
但是,当研究人员开始对那些与人类有着惊人差异的生物(如章鱼和乌贼)进行基因组测序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章鱼和乌贼的眼睛[24]与我们的眼睛极其相似。事实证明,章鱼和乌贼眼睛的突变基础与PAX6基因不同,但二者间又有很高相似性。被闪电击中已经是极小概率事件了,而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同一个基因被闪电击中了两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约6亿年前,人类与章鱼和乌贼在进化轨迹上分道扬镳,但最终我们都拥有了相似的眼睛。这并不是因为人类与章鱼和乌贼都抽中了进化的彩票,我们真正得到的启示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大自然有时会趋向于“提供”同类解决方案,因为有效解决方案只有这么多种。这一洞悉至关重要,因为它表明,有时一些小意外造成的“颠簸”最终会被消除。既然章鱼或乌贼的眼睛和人类的眼睛基本上一样,那么也许微小的变化并不重要。偶然性可能会改变某些事情发生的方式,但最后结果是相似的。这就好像早上按下闹钟的贪睡按钮可能会耽误你上班,但是不会改变你的人生道路一样。无论如何,你都会到达同一个目的地,这就是趋同性。
“趋同”代表了进化生物学中“万事皆有因”学派,而“发散”则代表了“事情就是如此”(没什么“必然如此”的原因)学派。
这一框架对于我们认识自己大有裨益。如果我们的生活遵循发散规则,那么生活上的微小波动也会对我们的职业轨迹、结婚对象和子女等方方面面产生巨大影响。但如果遵循的是趋同规则,那么随机或意外事件仅可能引起一些奇异的小插曲,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忽略这些偶然的因素。
几个世纪以来,一种能反映趋同信念的世界观——强调某些事物具有不可动摇性——主导着人们看待科学和社会的方式。牛顿定律不应该被打破;亚当·斯密曾写道,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我们的行为;生物学家们最初反对达尔文的理论,原因之一是自然选择假说太过于看重随机,而很少强调优雅的秩序。长期以来,不确定性一直被理性选择理论和机械模型所排挤。我们把微小的变动视为“噪声”而将其忽略,这样就可以专注于研究真正的“信号”。甚至我们的名言也灌注了简洁的趋同逻辑,例如,“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终会向正义弯曲”[25]。我们被告知,正义是不会被随意弯曲的。
几十年前,一位进化研究领域的“异端者”木村资生向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他坚持认为,微小、任意、随机的波动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木村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少年的他似乎并没有注定要从事学术研究。他讨厌上学,因为当时的教育体系要求学生必须遵从学术界公认的知识。尝试新思想的学生可能会受到惩处,知识传承于权威,这意味着秩序和确定性。木村天性好奇,但他的学校容不下他这好奇的头脑。不过,在1937年,木村受到一位老师的鼓舞,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学术热情,他发誓终身致力于揭开植物的秘密。[26]
1939年,木村全家遭遇了一次严重的食物中毒,[27]他的兄弟甚至因此丧命,木村也不得不在家中卧床休养。由于无法继续研究植物,木村开始阅读数学、遗传和染色体方面的书籍,他对植物的着迷逐渐转变为对基因以及基因突变问题的痴迷。可以说,木村的事业轨迹(包括他后来在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都是由这顿变质的饭开启的。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进化生物学者,木村仔细研究了生命的分子结构单元。随着观察的深入,他越发怀疑基因突变并没有多少规律和原因可循。木村察觉到,许多突变既无益也无害,这些变化往往是随机的、中性的,且毫无意义的。[28]每当突变发生时,木村的前辈们都会搜寻相应的解释和原因,以便让突变“说得通”。对此,木村只是耸耸肩:有些事情的发生没有原因,事情就是这样。
木村的发现重塑了进化生物学领域,带来了影响几代学者的新观念,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木村的学术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也许不是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原因,也许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最小的变化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
木村自身的经历也是其学术思想的生动例证。他的经历形象地表明,随意、相互关联的变化会如何导致偶然事件的发生。1944年,木村离家去上大学,他希望避免被征召入伍。1945年8月,他正是一名京都大学的在校生。如果史汀生夫妇错过了1926年去京都的火车,转为到大阪度假,木村和他的想法很可能会被湮灭在原子弹的耀眼光芒之中。
[1] O. Cary,“The Sparing of Kyoto — Mr. Stimson’s ‘Pet City,’”Japan Quarterly 22 (4) (1975): 337, https://www.proquest.com/scholarly-journals/sparing kyoto-mr-stimsons-pet-city/docview/1304279553/se-2. See also J. M.Kelly,“Why Did Henry Stimson Spare Kyoto from the Bomb? Confusion in Postwar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 (2)(2012): 183–203.
[2] “Summary of Target Committee Meetings on 10 May and 11 May 1945,”top-secret memo of the United States Target Committee, 12 May 1945,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162/6.pdf.
[3] Alex Wellerstein,“The Kyoto Misconception,” Restricted Data: The Nuclear Secrecy Blog, 8 August 2014.
[4] Ibid.
[5] 即美国陆军部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译者注
[6] “The Interim Committee,”Atomic Heritage Foundation, 5 June 2014.
[7] Kelly,“Why Did Henry Stimson Spare?”
[8] B. J. Bernstein.“The Atomic Bombings Reconsidered,” Foreign Affairs 74(1) (1995): 135–52, https://doi.org/10.2307/20047025.
[9] Cary,“Sparing of Kyoto,”337.
[10] Alex Wellerstein,“Nagasaki: The Last Bomb,” New Yorker, 7 August 2015.
[11] Alex Wellerstein,“The Luck of Kokura,” Restricted Data: The Nuclear Secrecy Blog, 22 August 2014.
[12] J. L. Borges,“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in Collected Fictio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2).
[13]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v.“Friedrich Nietzsche,”17 March 2017,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nietzsche/.
[14] 尼采的哲学思想,认为一切发生的事情最终都有益处,因此人们应该接受和拥抱命运。——译者注
[15] “Terrible Act of Insane Woman,”Manitoba Free Press, 17 June 1905.
[16] Richard Dawkins, Unweaving the Rainbow: Science, Delusion and the Appetite for Wonder (London: Houghton Miflin, 1998).
[17] Michael Holroyd, Bernard Shaw: The One-Volume Definitive Edition(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18]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19] R. Black, The Last Days of the Dinosaurs: An Asteroid, Extinc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Our World (Cheltenham, UK: History Press, 2022).
[20] Ibid.
[21] Martha Henriques,“How Mammals Won the Dinosaurs’ World,” BBC Future, 15 August 2022.
[22] Lisa Randall, Dark Matter and the Dinosaurs: The Astounding Intercon nectedness of the Univer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7).
[23] W. J. Gehring,“The Evolution of Vision,”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Developmental Biology 3 (1) (2014): 1–40.
[24] A. Ogura, K. Ikeo, and T. Gojobori,“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e Ex pression for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Camera Eye between Octopus and Human,” Genome Research 14 (8) (2004): 1555–61.
[25]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Remaining Awake through a Great Revolu tion,”speech given at the National Cathedral, 31 March 1968.
[26] Tomoko Y. Steen,“Always an Eccentric? A Brief Biography of Motoo Kimura,” Journal of Genetics 75 (1) (1996): 19–25.
[27] Ibid.
[28] M. Kimura, The 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