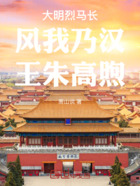
第62章 真是开窍了啊
只见朱棣这个惯于巧设阴谋、善使奸诈手段的人物,又再度故技重施,搬出那老掉牙的一套,以发配凤阳高墙来威胁朱高煦。朱高煦内心深处那股汹涌澎湃的怒火,瞬间就如火山喷发一般,炽热而猛烈,恨不能即刻扬起手掌,狠狠扇过去一个大巴掌。然而,转念之间,他意识到面前站立的毕竟是尊贵无比、权势滔天的永乐大帝,这股几近失控的冲动也只能被死死地压抑在心底,暂且偃旗息鼓。哼,咱这宽宏大量的汉王爷,才不屑于跟他一般见识!无奈之下,朱高煦只得犹如陷入困境的困兽,拼命地开动脑筋,绞尽脑汁地思索着应对的策略。
金忠、夏元吉等诸位位高权重的大佬见此情景,也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正在进行的议论。他们一个个心怀好奇,犹如好奇的孩童渴望探寻神秘的宝藏,都想瞧瞧在不可违背太祖旧制这一犹如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前提之下,这位汉王爷究竟能够想出何种高明绝妙的法子来化解难题。金忠坐在夏元吉身旁,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急切,忍不住压低嗓音问道:“对于此事,夏尚书您可有什么高妙非凡的见解?”
夏元吉的面色凝重至极,仿佛承载着千钧重担,缓缓开口说道:“我朝当下所施行的税制,乃是沿袭了唐宋时期的‘两税法’。在立国之初,为了让那因战乱而遭受重创、满目疮痍的民生得以逐步恢复,精心制定了赋役法。一切均以黄册作为根本依据,黄册之中有人丁就意味着存在徭役,有田地就必然有相应的租税。”
“待到民生渐次复苏,宛如寒冬过后的大地迎来温暖的春风,万物开始焕发生机。这才以‘两税法’作为稳固的基石,逐步对税制进行细致的完善。对待田赋,乃是依据田地的亩数来征收,南北之间由于地域、风土人情等方面存在差异,通常是在夏秋这两个季节进行征收,此乃极为关键且重要的税收来源。”
“而征收赋税的根本凭据,便是那十年大规模编制一次的赋役黄册,以及那详细记录土地状况的鱼鳞图册。”
夏元吉稍稍停顿,深深叹了口气,这口气仿佛带着无尽的沉重与无奈,接着说道:“此事牵涉到赋税的征收,实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在不违背太祖旧制的前提之下,妥善、完美地化解此等棘手且复杂的难题,近乎是一件几乎无法达成的艰难之事。”
金忠闻听此言,脸色微微一变,那细微的变化仿佛是平静湖面上泛起的一丝涟漪。他伸手轻抚胡须,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不再发表任何言论。赋税征收若出现问题,那必然要对赋税制度进行变革。但革新税制这等惊天动地、影响深远的大事,如同触动一张紧密交织的大网,稍有不慎便会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绝对不可贸然行事。
那么,汉王朱高煦,究竟会有怎样的高见呢?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如同聚焦的光束一般,紧紧地聚焦在朱高煦身上。有人满心期待,目光中充满了热切的盼望,盼着他能够口出惊人之语,成功化解这赋税征收的极度棘手的难题;有人则是满脸戏谑与嘲讽,那表情仿佛在等待一场闹剧的上演,就等着看他出丑闹笑话。
朱棣亦是满怀期待地看着他,心中暗自祈盼着这个好似突然开窍、灵光乍现的儿子,能够再度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良久之后,朱高煦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世间的智慧都吸入胸膛,然后转过头,目光坚定地看向夏元吉。
“老夏头,你可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化解眼前的困局?”
众人听了这话,顿时一阵无语。敢情您老闷头思考了半天,最后愣是一个有用的点子都没琢磨出来?
夏元吉苦笑着摇了摇头,那苦涩的笑容仿佛是深秋的寒风,带着丝丝凉意。他将方才对金忠所说的话又一字不差地重新复述了一遍,每一个字都如同沉重的石块,砸在众人的心间。
眼见这位声名赫赫、备受尊崇的名臣也束手无策,朱高煦顿时咧嘴笑了起来,那笑容中带着几分不羁与放肆:“老夏头,你这户部尚书也不过如此,看来也不顶用啊!”
夏元吉那张历经岁月沧桑的老脸瞬间涨得通红,犹如熟透的苹果,却是有口难言,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只得尴尬地杵在原地,那模样仿佛是风中的残烛,孤独而无奈。
朱棣见此情景,狠狠地瞪了朱高煦一眼,那眼神犹如锋利的刀刃,充满了威严与恼怒。刚要开口如雷霆般狠狠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口无遮拦的混小子一番,却听到他笑着说道:“其实这事儿没那么复杂,用不着大张旗鼓地对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只需在征收制度上面做个小小的、巧妙的改动就行!”
一众大佬听闻此言,瞬间都愣住了,神情变得极为丰富多样,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不会吧?难道他真有切实可行的办法?连户部尚书夏元吉都觉得棘手、深感无力应对的难题,汉王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想到了解决之策?那一张张脸上写满了怀疑、震惊与期待,仿佛是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充满了未知与迷茫。
原本朱棣那些斥责他的话语已经涌到了嘴边,犹如汹涌的潮水即将决堤,听到这话却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那憋在心里的气让他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憋得那叫一个难受,犹如鲠在喉间的鱼刺,上不得下不得。
“行了,赶紧说,别卖关子了!”
朱高煦撇了撇嘴,那神情带着几分不屑与自信,声音低沉而有力,仿佛是从幽深的山谷中传来:“大家都心知肚明,朝廷的赋役征收主要是以人户为中心的赋役黄册为主导,以土地为中心的鱼鳞图册为辅助,二者相辅相成,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互为经纬,紧密相连。”
“因而,户帖和黄册制度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朝廷重要的赋税征收凭据,这一点毋庸置疑,对吧?”
夏元吉连连点头,眼中的惊喜之色愈发浓烈,犹如夜空中绽放的璀璨烟火。汉王能如此清晰、深刻地意识到这关键所在,那就表明他绝非是信口雌黄、毫无头绪!说不定这个往日里看似鲁莽冲动的家伙,还真能令人刮目相看,如那蒙尘的明珠在关键时刻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朱棣微微颔首,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意仿佛是春日里的微风,温暖而又充满鼓励,示意他继续阐述下去。
“然而,自永乐年间起始,民户人丁犹如雨后春笋般急剧增长,田地的状况亦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犹如汹涌澎湃的海浪冲击着坚固的海岸。再者,于攒造册籍与推收钱粮的漫长而复杂的进程中,诸如户书、粮书、里书、甲书等吏役人等从中舞弊,如同隐藏在黑暗中的贪婪蛀虫,一点点侵蚀着制度的根基。活着的人未能及时补充登记入册,离世的人也未按照规定被勾销,田地的买卖、抵押等种种情形都未能如实登录在册。这般下来,黄册制度渐次陷入了紊乱与废弛的尴尬境地,徒有其名,实则成了虚假无用、毫无价值的伪册!”
伪册!
这个词汇,恰似一把锐利无比、寒气逼人的剑,深深地刺痛了在场众人的内心,那疼痛犹如电流瞬间传遍全身,令人不禁心头一颤。
户部尚书夏元吉大惊失色,那脸上的表情犹如被晴天霹雳击中,当即提出强烈的异议:“汉王殿下,黄册户贴乃是十年一大造,怎会沦为毫无作用的伪册……”
“老夏头啊,您就别再嘴硬啦。信不信本王此刻随意从各地州府中抽取黄册,上面所罗列的人户姓名和事产,依旧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姓名和数目,内容压根就没有半分实质性的变化?”
此话一出,夏元吉神情呆滞,仿佛灵魂瞬间被抽离,脸上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的神色,那瞪大的双眼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看穿,却又感到无比的迷茫与困惑。
“洪武初年大规模编制黄册之际,太祖爷未任用当地官员去核查田亩的数量,而是启用了众多的监生。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与士绅豪强相互勾结,瞒报田亩的数目从而少交赋税。所以那一次的黄册乃至洪武年间的黄册,皆是真实可信、毫无虚假的。就好比当下这河南赈灾金一案,那些贪婪无度、毫无良知的贪官污吏,连赈灾金都敢肆意染指,他们又岂会在意什么黄册鱼鳞图?
“老二,既然这些黄册大多弄虚作假,那赶快说说你的应对之策吧。”
朱棣沉吟片刻,眉头紧紧拧成一团,仿佛是纠结在一起的绳索,怎么也解不开。黄册与鱼鳞图册,乃是朝廷征收赋税的重要依凭和坚实基础。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甚至是贪污腐化,致使这些黄册成为了毫无价值、不具任何真实性的伪册!
可即便朱棣这位天子深知此中状况,眼下他也苦无良策,犹如迷失在茫茫大雾中的旅人,找不到前行的方向。难道要下令对全国各地的黄册逐一进行严格清查?那无疑将是一项耗费海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浩大工程,如同移山填海般艰难无比!然而真要如此行事,只怕最终会得不偿失,犹如投入无底深渊的巨石,连一丝回响都听不到。
所有人都眉头紧锁,那一道道皱纹仿佛是历史的刻痕,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朱高煦,那目光中充满了期待与疑惑。
汉王爷微微一笑,那笑容中带着从容与自信,语调沉稳有力地说道:“既然黄册已成毫无作用的伪册,那朝廷就重新制作真实有效、切实可行的实册!”
“老夏头,让各道州府的县官拟定一道详尽的计划册。每年秋粮征收之时,地方上八月出具细致的预算计划册,九月精心编制花户实征册,并认真填写准确的通知单。十一月起朝廷开始有条不紊地征粮并按户填册,十二月征收结束后将实征册及时呈交朝廷。”
“征粮结束之后,朝廷会对计划册和实征册进行严格、细致的核对。倘若二者相较之下存在任何出入,不管是数量过多还是过少,皆可责令地方官员给出合理的解释。若解释不清,便可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夏元吉听了,先是一愣,那短暂的失神仿佛是思绪的瞬间短路,紧接着兴奋地点了点头,那点头的动作充满了力量与期待。这个法子,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官员谎报或者利用灾情贪腐的难度,如同给他们戴上了沉重的枷锁,让他们难以肆意妄为。既增加了朝廷的收入,又有效地遏制了恶劣的贪腐状况,而且还未曾对太祖旧制做出丝毫改动,简直就是化解当前困境的绝佳策略,如同一剂对症的良药,恰到好处,药到病除!
金忠等人颇为惊讶地看着朱高煦,眼神中满是质疑,仿佛是头一回真正认识他一般,那目光中带着重新审视与深入思考。
朱棣同样满脸惊色,他着实未曾料到,自家这个往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看似鲁莽冲动的老二,居然能够提出如此精妙绝伦、深思熟虑的主意。
这个家伙,当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诸位爱卿,此计策究竟如何?”
朱棣心情大好,那脸上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温暖而又充满喜悦,笑眯眯地问道,引得群臣纷纷点头称赞,那此起彼伏的声音仿佛是一阵和谐的乐章,在朝堂之上回荡。
“既然如此,那就即刻拟旨,将其在天下广泛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