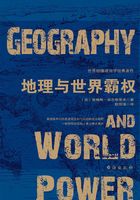
第5章 道路:巴勒斯坦和腓尼基
我们已经指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所以出现了两个文明中心,是因为两个地区的地理条件,都让生活在这里的民族拥有了一种整体上高于其他民族的优势。这两个文明中心的出现,尤其是后者的崛起,还对附近其他地区的民族产生了影响。当然,生活在两地之间的那些民族受到的影响,或许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其他民族受到的影响那么巨大,可它们受到的影响却更加持久,故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也更加有效。
尽管埃及的两侧都是几乎不可逾越的沙漠,但在埃及东北角的地中海沿岸,沙漠边缘所在的海滨地区却不像其他地方那样荒无人烟,并且向遥远的北方延伸,逐渐变成了一片土地肥沃、雨水相当充沛、海拔很低的沿海之地和内陆丘陵;这里,就是腓力斯丁人(Philistines)、希伯来人(Hebrews)和腓尼基人的家园。这个地区,构成了连接那两个伟大的早期文明中心的纽带,并且因这一事实而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如此一来,在研究文明进步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开始接触到另一种地理制约因素了。从可以利用更多能量这一意义上来看,人类非但是在那些最容易生存下去的地方生活,而且会朝着最容易运动、运动所耗能量最少的方向前进。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运动往往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有马路的时候,人们会沿着马路行走;但在出现马路的很久以前,世间其实早已有了一些路线,由于地理分布情况使然,人类沿着这些路线行进起来,要比沿着其他路线更为轻松。它们都是道路,而不是马路。马路都有数英尺或者好几码宽,可道路却没有固定的宽度。一个房间里有道路从门口通往壁炉,我们可以行走其间而不会碰到任何障碍,可房间里却没有马路。两地之间可能只有一条道路,却有许多的马路。从伦敦通往苏格兰的道路位于亨伯河(Humber)与奔宁山脉(Pennines)之间,一路向北,经过约克(York)平原和纽卡斯尔(Newcastle)平原,绕过海岸抵达爱丁堡(Edinburgh)。而“大北路”(The Great North Road)过去和现在都只是这条道路的一种形式;“大北铁路”(the Great Northern Railway)及其各条支线,则是与之相对应的“铁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没有直通埃及的马路,却有数条非常明确的道路,其中有一段距离,这些道路还合而为一了。从巴比伦往幼发拉底河河谷上游走,然后横至夹在黎巴嫩山脉(Lebanon)与外黎巴嫩山脉(Anti-Lebanon)之间的奥伦特(Orontes)河谷,再沿着莱昂特斯河(Leontes)与上约旦河(Upper Jordan)河谷南下,穿过埃斯德赖隆(Esdraelon)平原,经过这个小小世界诸军集结之处的米吉多(Megiddo)或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穿过地中海沿岸腓力斯丁人的聚居之地,再越过那条狭长的沙漠地带,然后抵达埃及,这条道路相对比较便捷。对于已经达到某种文明程度的商人而言,虽说越过叙利亚沙漠狭窄的北端前往大马士革(Damascus)绿洲不那么容易,但路程较短,因而更加节省能量;大马士革绿洲既是一个起点,因为人们可以从这里出发,越过沙漠往东,也是西部的一个登陆点,还是叙利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那些商人是如何来到此地的,他们全都经过了埃斯德赖隆平原和非利士(Philistia)地区。
这条“道路”,并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重要起来的;它的重要性,是随着道路两侧各地重要性的增加而日益发展的。我们也不能以为,这条道路的交通量达到了英国一条乡间马路那样的交通量;不过,当时世界上的那种贸易中,最大的份额就是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这条道路”经过的那些地区,全都拥有一种像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样的早期历史。这些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它们在彼此开始接触之前,必定有过一种高级文明,而它们的影响范围,必定也很广泛。即便是在那个时代,双方之间的首次接触,似乎也纯属偶然。在埃及第四王朝和阿卡德的萨尔贡王治下时期,也就是说公元前3800年左右,两个地区都曾派遣远征队前往西奈半岛(Sinai)上的沙漠去开采铜矿,或者开采适合用于雕塑的石头。不过,随着岁月流逝,人们开始经由“这条道路”从事贸易,而军队也开始由此挺进,所以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世界要地的那3000年里,黎凡特(Levant)[15]南部这些肥沃富庶的沿海地区,便逐渐获得了与其大小完全不相称的重要地位。由于这里是腓力斯丁人和以色列人(Israelites)的家园,是连接古代世界两个帝国之间的门户,故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地位显赫,就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情;但巴勒斯坦地区本身非常狭小,因此我们都听说过,以利亚(Elijah)[16]在一天之内就能从这头跑到那头呢。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都曾在不同的时期宣示过它们的宗主国权威,但即便是在那种时候,两地对属国的控制也并非始终都很有效,而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这条道路”经过的地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也都是由一些不向任何一国效忠的民族占领着;起初,这些民族彼此之间征伐不断,后来是因为认识到经由各民族内部进行的贸易带来了诸多好处,它们才逐渐变得文明起来。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大卫(David)和所罗门(Solomon)统治时期,古埃及与古亚述势力日衰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与沿海民族腓力斯丁人相对而言的山区民族以色列人,才极其有效地控制了“这条道路”,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古代世界其他帝国相媲美的帝国。这个王国分裂成两个部分之后,便丧失了对“这条道路”的有效控制,再次变成了邻近地区一个小小的山地国家;尽管它的确处在中心位置,可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希伯来人的这个王国先是向两个伟大帝国中的一个俯首称臣,后来又倒向了另一个帝国,最终还在两个帝国的争斗当中垮了台。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臣服于其他帝国之后,它们之间的那条道路在地理上也变得几乎毫不重要了;但耶路撒冷必定始终都极其重要,至于原因,我们在此不太感兴趣,故不作论述。
有一种相关的地理条件,接下来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影响;这种条件,取决于地球上的水陆分布情况。很显然,人类只能生活在陆地上。国家必须位于陆地上,因此历史首先且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陆地。不过,尽管不可能有大量人口永久生活于水上,也不可能有益地利用能量并拥有一种水上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在水上进行与定居相对而言的运动,却要比在陆地上容易得多。陆地上有阻碍交通的种种障碍,人们必须越过这些障碍,或者必须绕道以避开这些障碍才行;可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使用的能量都不会带来充足的回报。不但如此,在水上移动给定数量的东西所需的能量,还要远远少于在陆地上移动这些东西所需的能量。也就是说,水面比陆地更适于形成“一条道路”,将人们与货物从此地运往彼地。
早期的那两个帝国,都很清楚这一事实。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非但提供了灌溉用水,满足了人类更加直接的个人用水需求,而且人们发现,它们也是道路。一开始的时候,人类使用的仅仅是由一捆捆芦苇制成的筏子,接下来人类又开始使用浮力更大的囊袋;后来,人类还开始利用轻舟,而公元前3000年时的古巴比伦商人甚至有可能非常大胆,可能驾驶着那种轻舟,进入了波斯湾(Persian Gulf)这片受到了保护的水域;一两百年之后,古埃及人无疑也曾驾驶一些船只,在红海(Red Sea)之上游弋。然而,这些方面都属例外情况,人们谈及的时候也是带着惊讶之情。当时,舟船其实只能在河流上行驶。
尽管在河流上驾驶舟船要比在陆地上来去所耗的能量更少,但这种交通方式也存在一种弊端,那就是人们只能前往有河流经过的地方。所有的河流,尤其是像幼发拉底河、尼罗河这种支流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支流的河流,即便是有运河加以辅助,其作用也不可能像海洋那么巨大;因为一旦到了茫茫的大海上,人类就可以前往天涯海角了。所以,地理上的水陆分布情况极其重要,而此种分布情况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海上交通之所以很容易,完全是因为海洋是一个整体,而陆地却为数众多。
不过,对古时那些民族而言,即便是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之后,未知事物的神秘性也仍然让他们无法更多地去了解大海。每个人都熟悉陆地,而人类生活的富饶之地与大海之间,却有沼泽阻隔。人们都熟悉流经陆地的河流,可没人了解大海;到海上去探险,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人类真正探索了大海之后,他们就是做出了世界上的一次伟大发现;此后,海洋就变成了历史中的组成部分。海洋不再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而是变成了一种纽带,将周边的所有陆地都联成了一体。
正是生活在通往海滨的那条伟大的陆上“道路”沿线的民族,真正率先做出了发现,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处的山脉脚下,是一片土地肥沃却很狭窄的沿海地带,且其边缘没有沼泽;这里的海洋,也非常深邃。因此,生活在这片陆地上的民族始终都看得见大海;他们不得不想到大海,而他们乘坐船只前往茫茫深海上,也远不如比前往其他地方那样麻烦。
人类如此发现的那个海洋,就是地中海(Mediterranean);这一点,也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正如许多人业已指出的那样,这里是一个可以让人类学到航海技术,而非只是学到河运技术的地方。顾名思义,地中海位于陆地之间;由于它是一个内海,因此非但这里的风暴没有开阔洋面上的风暴那样威力巨大,而且对古时那些水手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是一个没有潮汐的海洋,因此小型船只(当时所用的全都是小船)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够轻而易举地登岸。这些有利条件,就是地中海、波斯湾与红海的共同点,但重要的是,地中海的面积要比波斯湾和红海广袤得多。不过,地中海还具有其余两个内海都不具有的一些优势。地中海沿岸的土地,整体来看要肥沃得多,而且沿岸不乏优质的天然海港;这里的海岸线上,有许多突出的岬角和众多的岬湾,还有众多岛屿耸立于各处水域,在人们需要登陆的时候,陆地始终都不会远得看不见,始终都可以让人们躲避风雨。这里,正是一个十足的水手摇篮。
人们发现地中海是一条“道路”之后,那个交界地区和起点之地上的民族,即生活在提尔(Tyre)、西顿(Sidon)以及其他城邦的腓尼基人,便成了古代这个小小世界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显然可以料想到,以海洋为根基的文明形式,出现的时间理应晚于我们迄今谈及的那些文明形式。自然,只有在人们认识到了那条“道路”的重要性之后,这些城邦才能发展起来;此后,必定又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人类的思想才会受到相关观念的刺激,才会去付诸行动。然而,到了公元前1600年,腓尼基人已是远近闻名的海上商人,所以,他们必定是在此前很久就开始了这种冒险的职业。有可能,他们起初是沿着这条“道路”从巴比伦王国而来的;他们在巴比伦熟悉了船只和贸易,那里晴朗湛蓝的天空促使人们对天文进行了研究,而天文知识又发挥出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可以在黑夜之中为他们的船只导航。果真如此的话,他们所处的新环境,就会激励他们继续朝着新的方向前进。在沿海地区那些星罗棋布的城邦当中,先是西顿独领风骚,接着又是提尔领先;腓尼基人的船只,便是从这些沿海地区出发,前往越来越遥远的蛮荒之地。有可能,他们最初是前去寻找贝类,因为皇家的袍裾需要染成“提尔紫”,因此对贝类的需求量一直都在不断地增长。
但不管怎样,寻找染料都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贸易或商业,只要获得的回报抵得上所吃的苦头,人们都会欣然从之;而腓尼基人进行贸易时可能也比较安全,还在地中海东西两端之间建立了许多的殖民地,因此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尽管松散却是一个整体、不容其他民族小觑的腓尼基人联盟。诚然,他们统治的疆域面积狭小,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商人,而商人是不需要面积广袤的肥沃土地来种植粮食作物的;他们可以用做生意赚来的利润,去购买粮食。提尔、西顿和迦太基,各自都只是统治着其周边的一小片地区,并且它们的领土也不像古埃及和巴比伦王国那样,并不是一个紧凑的整体;它们的领土散布在地中海沿岸各地,而后者则将这些孤立的地区团结成了一个政权,且这个政权的秩序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个国家。
不但腓尼基人登台掌权是一件新鲜事,而且每个腓尼基人身上都具有种种新的道德品质;这些品质,同样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培育出来的。蛮夷之地的市场如此持久地一直欢迎他们,说明他们的行为必定博得了那些野蛮民族的敬重。贸易基本上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只知道这一点。但腓尼基人懂得更多;他们学会了勇敢无畏,却并不像古亚述人一样仅仅是逞强好斗。常年驾驶着脆弱的船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非但让他们培育出了一种高尚的勇敢精神,还培养出了一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正是这种勇敢与热爱自由的品质,使得他们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抵挡住了亚述军队的淫威。
尽管亚述帝国没有吞并腓尼基的贸易,可对于自己无法攫取的这种贸易,亚述帝国却尽力进行了破坏;故自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腓尼基的腓尼基人就衰落下去了。然而,一直要到不得不面对一个海上强国之时,他们才最终灭亡;现在,我们必须探究这个海上强国的历史了。